主持人语
南京的秋天,并不典型。天气明显凉了一些,但热似乎仍然是一种主旋律,但这热又并不稳定,仿佛往前稍稍再迈一小步,寒意便也会扑面而来了。南京的秋天,是混杂的,也是“散装”的。
朱苑清的长篇小说《黑镜森林》,和南京的秋天一样,也有这样一种混杂的、散装的特点。它不纯然是现实主义的,也并非典型的现代主义,而是一种“超纤魔幻现实主义”(腰封语)。本期“新作大家谈”我们邀请了翟业军、方岩、何同彬、来颖燕、刘诗宇五位青年评论家,就这部小说进行畅谈。
我还记得朱苑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被太阳晒热》,这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但名字看上去却略显抽象,这个名字出自于我们故去的好友黄孝阳之手。《黑镜森林》则在现实的基础上,又向前跨越了很多,这一次,朱苑清是以具体的写作去实践黄孝阳曾经心心念念的“量子文学”。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我是否可以将朱苑清的《黑镜森林》看作是对黄孝阳的致敬之作?
《黑镜森林》仅从题目来看,就极具象征的深意,对于“黑镜”,翟业军的阐释极为生动准确,他说:“一面不再揭示真相、说出真理的镜子,就是一面‘黑镜’。‘黑镜’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被打磨成一面镜子的可能,它不再试图反映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跟客观世界形同陌路的世界——这样的‘黑镜’就是一面‘反镜之镜’。”对于“森林”一词,他亦有一种深刻的理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黑镜森林》在叙事上别有用心、极富特色,这在书的设计和印刷上都有体现,蓝色和黑色字体的交叉,既是现实和梦境的交织,也是观念和技法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不可尽知慢慢地呈现出来,并最终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自然万物间所拥有的不可尽知的联系——黑暗深处,一切都未可知,但一切都在发生。这自成一体的哲学观被作者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在思想的维度也在形式的维度上。”(来颖燕)
说实话,这是一本并不太容易读懂的小说,或者说,这是一本有阅读门槛的小说,但我并不担心它会吓跑那些真正喜欢小说的读者,因为在它先锋的外衣之下,依然有着和现实的某种深切的关联,甚至于还有着一种倾向于读者的“类型化”特征。“读《黑镜森林》时,我下意识联想、互文的并非文学史上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而是在青春期曾热爱的类型叙事,在如今消闲时仍会选择的其他艺术形式。”(刘诗宇)
毫无疑问,《黑镜森林》和当下大多数青年小说家的写作相比,有着更为鲜明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甚至于有点剑走偏锋。但这可能正是我们当下青年写作所缺少的一种艺术抱负和叙事勇气。“我们在《黑镜森林》中看到的现实梦境、莫比乌斯环带结构、拼图式结构、量子文学……无不显现着一种特别的叙事野心:对小说边界的叩击、对现实主义叙事秩序的逃逸、对现实和人性晦暗的凝视、对一切生命中异质性和创造性的渴望。”(何同彬)
朱苑清在其创作谈中,谈到了黄孝阳,几位青年评论家也或多或少地都谈到了黄孝阳,我能想象得到他如果能看到这几年整个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定是兴高采烈的,甚至于他一定又会大谈特谈他的“量子文学”,直到把我们谈崩溃为止。我甚至也能想象得到,如果黄孝阳能够读到《黑镜森林》,一定会拍案叫好,也定会逢人都要推荐。
这当然只能是想象,但我确信,写作者和写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如同‘量子纠缠’,我们无法描述原因和路径,却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发现能量完成了传递。”(方岩)

在《黑镜森林》中,朱苑清拉了一下灯绳,关掉了打向真相的灯源,于是,真相死了,被抛弃了。其实,不必说拉灯绳的后果,拉灯绳这一动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宣判:剧场的一片黢黑中本无所谓真相,这时候,一束光打向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以被这束光所勾画、烘托出来的样子活了,舒展了,开口说话了,他/她好像就是此时此刻的绝对的、唯一的真相,殊不知这一切只是导演所要的效果而已,导演一声令下,那个地方复归为空无。当打向真相的灯源被拉灭,世界不再有真相,世界的客观性本身跟着被打上问号的时候,一直以来颠扑不破的“镜子说”就被颠覆了——没有一个坚实的客观世界,何来对它的反映?反映又如何谈得上是否忠实?这样一来,《黑镜森林》就是拒绝真相、扑灭真相的,在它的世界里,所有自行宣称掌握真相的人,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一面不再揭示真相、说出真理的镜子,就是一面“黑镜”。“黑镜”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被打磨成一面镜子的可能,它不再试图反映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跟客观世界形同陌路的世界——这样的“黑镜”就是一面“反镜之镜”。更激进的设想是:客观世界不再坚实了,“黑镜”里的世界说不定更具客观性?
真相被勾销的直接后果,就是框架的坍塌。一个没有框架的世界就是一个无法被整饬、穿透并进而被理解的绝对混乱的世界,就像是一座万物都在本着自身的求生意志而生成、毁灭的“森林”。这样的“森林”里没有黑白、对错、真假、美丑、善恶的两分,就连现实与梦境的界限都不再清晰,而是彼此渗透、瓦解的——你能说得清黑色与蓝色的字体,哪个部分更坚实,更摄人心魄?大的框架坍塌,小的局部就诞生了,刘顺、筱英、杨红娟、毛小军、蒋老太、小丸子,这些局部为了获得自己的光和水,挣扎着、蠕动着、颤抖着,从而造就了一种绝对的动,无序的动,痉挛一样的动。动的世界如此生辣,因为每个局部为了自身的持存都已拼尽了全力;动的世界又是如此狰狞,因为局部与局部绝望地缠斗在一起,未有已时。如果想在动的世界里寻找到确定的东西的话,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每个局部的绝对的求生意志、权力意志;动的世界假如也有真理的话,真理就一定是虬曲的、缠绕的,无论如何也理不清,道不明。这样一来,小说的结尾就稍觉软弱了些,因为那阵风一路吹拂下去,试图给出一个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真相,希望找到一个笔直的因而也就是虚假的真理。

直到这群人在同一天登上了同一辆旅游大巴抵达了同一处景点时,过于戏剧性的巧合大概是在提醒现实主义原则开始消退。当所有已经暴露的问题开始以某种离奇的方式被解决时,故事开始变得惊悚:吴筱英离奇失踪;毛小军在湖中溺毙;蒋老太跌入山崖;而小丸子则毫无征兆地时不时闪现于某些场合……时空错乱、场景玄幻、凶手扑朔迷离。无疑,魔幻、悬疑乃至仙侠等类型故事的叙事手法和风格在其中叠加、拼接。最后,那辆大巴载着幸存者驶往未知之地,但也可能是拉着一群凶手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故事的结尾又成就了一出因果报应的劝诫寓言。
虽说《黑镜森林》是一部叙事类型多元、视角交错、寄托多重的长篇小说,但两个世界的边界并没有淹没于复杂的叙事线索之中:以小区生活为中心的故事皆发生于黯淡、压抑的现实世界;景区里那些怪诞惊奇的经历其实是一场梦境。两个世界的叙事交替进行,但作者朱苑清还是分别用黑字和蓝字区分了现实和梦境。倘若没有这种善意的提醒,两个世界对彼此的深入和淡出会显得更为顺滑、流畅,会形成一种亦真亦幻、虚实交错、浑然一体的叙事效果,用朱苑清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莫比乌斯环式的叙事进程。当然,被染色区分的叙事更像是两个世界的对峙,两个独立的叙事遵循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在运行,彼此映照、探询和质疑。
倘若把梦境视为现实的解决方案,那未免显得残暴酷烈,善恶是非在其间模糊乃至颠倒,梦境便成了现实的地狱。如果现实本就是地狱呢,种种困境积重难返,深陷其中的人都犹如绝望的野兽,那么,现实消失之处,便是人性泯灭之时,梦境便成了现实的宿命。宿命只是未来的一种,除此之外,未来还有别的样子吗?还有没有其他色彩的叙事呢?
第二天清晨,所有的人从梦中醒来,现实一切照旧,只有小丸子在风雨之夜溺毙了,黯淡的现实处境里唯一的亮色与希望瞬间熄灭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朱苑清何以要用黑色字体标注那些现实故事了。黑色吸收光谱内所有的可见光,也不反射任何颜色的光。
读完这个黑暗的故事准备合上书时,会发现封三上粘着一个黑色的纸袋,里面装着朱苑清的创作谈。这样的设计仿佛是朱苑清的不甘心,她在邀约我们一起把黑暗撕开一道口子。在创作谈中,她极其耐心地解释了她在写作上所进行的新尝试,其中有一半的篇幅在谈她对“量子文学”的理解。很显然,这个提法来自我们共同的好友黄孝阳。我一直认为,这种提法是一种夸张而晦涩的自我修辞,它涉及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对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和作家形象的想象性建构和命名。很难想象这种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阐释能在多大程度上向别人开放。直到朱苑清极其细致地说出了她的理解,以及它对自己写作的具体影响,我才意识到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的评鉴式阅读,远远难以企及一个作家对同行的拆解式揣摩。但无论如何,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隐秘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笃信和尊重,往往会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同“量子纠缠”,我们无法描述原因和路径,却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发现能量完成了传递。

所以,讨论《黑镜森林》一定要有一个发生学的视野,朱苑清这样一个文本实验色彩很重的小说作品,从一开始贯彻的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写作是一次生成事件”,也是在践行着黄孝阳所设定的“当代小说的任务”:“那些少有读者光临的小说深处,世间万有都在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而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件。”我们在《黑镜森林》中看到的现实梦境、莫比乌斯环带结构、拼图式结构、量子文学……无不显现着一种特别的叙事野心:对小说边界的叩击、对现实主义叙事秩序的逃逸、对现实和人性晦暗的凝视、对一切生命中异质性和创造性的渴望。
《黑镜森林》充满了罗兰·巴特所谓的小说写作的“幻想式”,朱苑清依赖的不是自己的既定的小说经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小说的文体内涵,更不是现在流行的泛现实主义写作的“惰性”,她的出发点是创作一种小说的理想形态,一种基于真实的现实体验和生命体验基础上的“小说的模拟”,因此整部作品都洋溢着一种叙事自由的内在快乐,以及这些自由在晦暗的时代经验中触礁、搁浅的种种“苦痛”。这种“幻想式”、这种注重写作的内在经验的属性(如同巴塔耶所说的“一种绝望的记述”,“进入意想不到之境,看到了眼睛未曾见到之物。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陶醉的了:笑与理性、恐怖与光明得以相互渗透……它完全不是我已知的东西,它能进入我的狂热之中。像一种绝妙的疯狂,死亡不停地打开或关闭着可能之物的大门”),也是在呼应着黄孝阳兄的“孤绝”:“小说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开始,一个人结束,甚至是一个人的阅读。”
最后,不得不说,作为在韩国学习电影的小说家,朱苑清在《黑镜森林》中运用了很多电影技法和视觉语言,而其晦暗、阴冷又坚硬的质地,也能让我们想到金基德、李沧东等韩国导演的影视作品。

在《黑镜森林》里,隐喻的力量驱动着故事的前进,而这些故事深嵌在我们的日常琐碎中,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形而上学越是现实,它就越是形而上。《黑镜森林》是对此的一次注脚和演绎。尽管小说中的一些地方在形而上和现实的融合度上还不够丰富和自然,但作者成功地向我们展呈了她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也提供了一个重建人性和世界的新的出口。

一、内核
接下来,请想象自己是如下三种人。
第一种,你是一个孩子。
父母、朋友、新衣服、新文具……身周小孩有的东西你都没有。
心情、身体、未来……他们身上被在乎的东西,在你这里都被忽略。
第二种,你是一个中年人。
平庸二字替换了你的姓和名,泥土缝里的屎蜣螂是你的肉身。
攒钱、攒钱……攒给那些在不远处向你招手的意外、病痛,攒给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的那个自己。
攒到只会因为钱而快乐、忧伤、庆祝、争吵的那天,攒到退休金发放那天,攒到所有欲望和快乐都油尽灯枯的那天。
攒到死的那一天。
第三种,你是一个老人。
在一个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的环境里,在一个旧的道德秩序不断崩溃的社会里,你无钱无势、老而不死,是为贼。
孙辈用着、吃着你不知道是什么的怪东西,说着、想着你理解不了的怪事情。
子辈明明吃饱穿暖,却仍为你不懂的事恐慌着。
你明明有手有脚,甚至比每天熬夜的子辈更健步如飞,却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帮不上。
如果你是如上三种人,且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你会想继续活下去吗?如果想的话,支撑你活下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二、叙事
如上三种人的命运,就是我穿越兼具先锋与类型气质的叙事形式,在朱苑清长篇小说《黑镜森林》中所看到的内核。
没错,我最喜欢的是这部作品的内核,以及使其得以彰显的丰富细节、生动笔墨,但我也必须承认其叙事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比内核更加“眩目”,这包括但不限于:
——将正文区分成了两种字体,一种是当下(梦境),一种是历史(现实);
——将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交织在一起;
——将几对“相爱相杀”式人物关系,在一个超现实的环境中集中引爆;
——用鬼门关等带有民俗恐怖气质的叙事元素,来呈现城乡、新旧时代的伦理冲突;
——用丧尸等带有西式恐怖气质的叙事元素,来增加小说的类型化气息和影视化感觉……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之间都应该保持同气相求的关系。古希腊的诗歌与戏剧、十九世纪的美术与音乐、二十世纪的文学与电影、二十一世纪的游戏与动漫,这些人类艺术史上的群星闪耀时无不如此。
当时的受众会特别幸福地发现,所有艺术形式看似关注着不同的事,但彼此知道这些不同之事都与自己沐浴在同一片阳光或月光之下。作家、艺术家虽然使用的是文字、笔触、影像、声音、代码等各种不同的载体,但就像一个人可以穿不同的衣服、拥有不同的身份,其灵魂总是深邃而恒一的。
从这个角度看,《黑镜森林》的叙事虽然并不完美,甚至其探索性反而可能让故事有“圆不回来”的逻辑危险,但我认为它是有意义的。
读《黑镜森林》时,我下意识联想、互文的并非文学史上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而是在青春期曾热爱的类型叙事,在如今消闲时仍会选择的其他艺术形式。
我认为这种感觉,可能正是我们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讨论“新大众文艺”,焦虑文学应该如何“破圈跨界”时需要的。
三、社会
虽然我欣赏《黑镜森林》中跨界的部分,但它终归还是一部文学作品。因此最后一部分还是回归文学的范畴,去寻找《黑镜森林》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中三种人浓缩的悲剧感,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小说最后把一切都归结为一场梦,所有的意外、所有死去的人都完好如初,回到故事开始的时间,但这并不能改变小说本身的悲剧气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叙事艺术中的时空倒转,绝大多数都是在强调问题本身的不可解决。
《黑镜森林》中的悲剧是带有时代性的。不被关怀的儿童、刻薄待己的中年、无所适从的老年——他们的悲剧既不是阿喀琉斯被射中脚踝、普罗米修斯被啃食心肠的悲壮,也不是《骆驼祥子》《1942》中的那种饥寒、战乱、死亡威胁下的悲惨,而是一种温饱实现之后、下一个历史阶段中的带有后现代气质的,钝感、温吞的悲剧感。
作为一部今天的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发掘和书写应该是必要的。
从新文学伊始,中国小说就始终带有浓郁的现实性和社会性。那些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作品往往要么带有群体层面的批判性,要么带有建构性,这几乎是衡量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狭隘的政治化视野。《黑镜森林》对群体悲剧的关注以及技术性书写,其实正意味着对这种文学传统的延续。只不过其含混、暧昧的部分对这种延续的完成度造成了一些影响,以至于我无法断言它就确切地完成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赋形,更不敢说它对于理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提供了足够的意义支撑。某种程度上,这不是《黑镜森林》的问题,而是当下大多数涉及到现实的作品的问题;又或者说,这也不是问题,当下文学在寻找到书写现实的“终极解法”——就像巴尔扎克写十九世纪,鲁郭茅巴老曹写民国——之前,必然会长期背负“温吞”“乏味”的指责,但是当答案浮现之际,之前种种就都变成了有效努力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黑镜森林》是一部既好读,又有意义的作品,哪怕它还并不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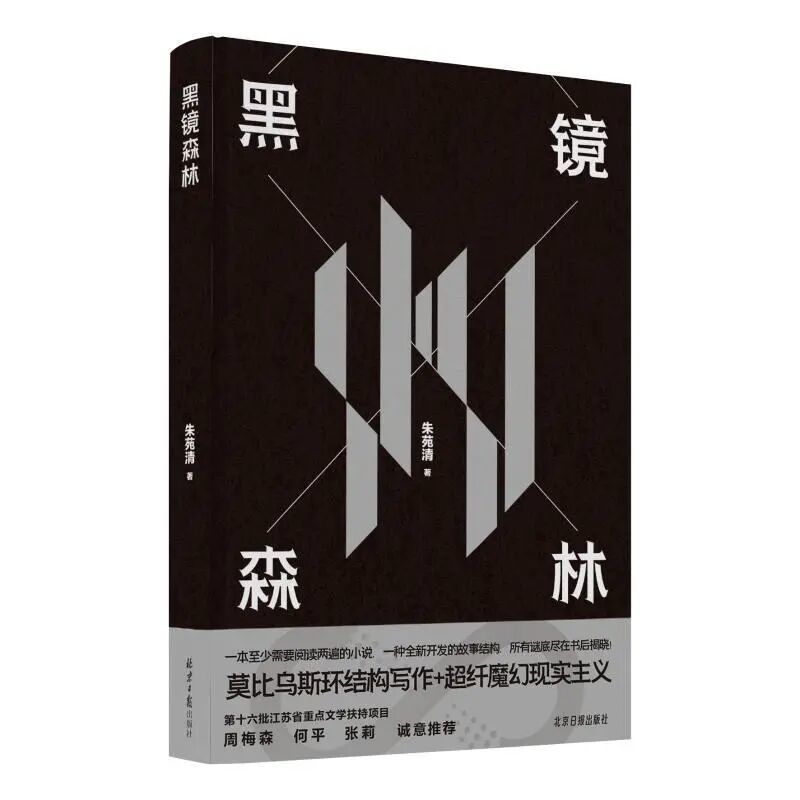
书名 :《黑镜森林》
作者:朱苑清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47748411
出版时间:2025年3月1日
《黑镜森林》讲述了储蓄所小职员刘顺长期困于经济压力,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次意外购买的"刮刮乐"彩票中奖后,他满怀欣喜地为夫妻二人订购了周末旅游团票,却因沟通方式失当引发激烈家庭矛盾。这场争执竟意外触发主人公进入诡谲的梦境维度,在虚实交织的超现实之旅中,他不断遭遇离奇死亡事件,逐渐揭开隐藏在日常压抑下的精神困境。 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我’是在全然不知自己处于梦境的状况下进行叙述并推进故事发展的。故事主线始终在梦境中展开并完成。虽然故事逻辑带有荒诞性,但通过辅线作为材料支撑,采用多视角拼贴的非线性叙事,还原了前夜主人公与邻居间的生活片段。这些现实突发事件正是诱发梦境的诱因,通过对它们的重组,虚实双线最终交织成具有真实感的死亡寓言。叙述技法上,作品创新性地实写梦境,将虚幻经历嵌入现实时间轴,同时将现实碎片重组融入梦境,形成叠化般的、亦真亦假的莫比乌斯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