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江苏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彰显出独特的叙事品格,在吴韵汉风文化根系上生发出具有鲜明辨识度的美学形态。作家们以文学经纬书写时代精神图谱,于历史纵深与现代转型的交织中开辟广阔叙事疆域。既见对非遗技艺传承的匠心摹写,亦有对城乡巨变的切片式观察;既烛照女性意识觉醒的幽微光谱,也镌刻新时代青年成长的精神轨迹。这些作品在赓续地域文化基因的同时,以开放视野突破创作藩篱,经由个体命运在时代浪潮中的浮沉嬗变,将微观生命史与宏观家国史熔铸成充满张力的复调叙事,最终铺陈出一幅传统根脉与现代气象交相辉映的文学长卷。
江苏作家始终将历史书写铭刻于文学基因深处,持续以自觉的史诗意识叩击文化脉络。2024年,其历史叙事更显突破性姿态,在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自觉中,跳脱线性史观的时空桎梏,转而以个体生命经验为棱镜,呈现出斑驳的历史光影。作家们摒弃纪念碑式的宏大叙事范式,通过家族史诗的绵长呼吸、市井传奇的烟火拾味与乡土寓言的伦理皱襞,构筑起多声部的历史言说体系,将深藏于历史褶皱的幽微人性,悉数置于文学探照灯的审视之下。
叶兆言的《璩家花园》以南京城南一座清代老宅为支点,将两个家庭、三代人的生命轨迹与重大历史事件相互交叠,撬动起百年沧桑巨变。作品通过对三代人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既呈现出代际之间人生观、价值观的承接与断裂,又刻画出人与人之间幽微隐秘的情感联结。作者以蘸满世情油彩的笔触,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得意失意描摹得浓墨重彩。主人公璩天井以老实木讷表象包裹赤子之心,在时代更迭中始终恪守情感本真,其“迟钝”与“专一”恰恰成为对抗历史虚无的精神锚点。小说对于南京城的文化肌理虽未专意铺陈,却随着人物穿行于秦淮街巷的寻常起居,悄然勾勒出一部流动的城市旁史。小说在文体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精妙糅合,跳跃的时间拼图打乱了常规叙事节奏,费教授日记构成的元叙事层叠出多重话语空间,目连戏《山河图》的文本嵌套则形成古今互鉴的叙事互文。小说既延续了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又以“说书人式”的通俗语言贴近市井声口,作品设置的叙事留白,既为小说增加了悬疑的元素,又在故意悬置间消解了类型化叙事的功利性,让故事回归生活本身的浑浊质感。
同样是以家族历史透视时代风云变幻,范小青的《不易堂》则以苏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为叙事背景,将历史考证与家族记忆交汇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追寻。小说通过“我”言子陈因研究课题“已毁古建筑群现状评估”重返离开多年的苏州故里,揭开苏州言氏祖宅“不易堂”背后的百年秘辛。作为清代《古城烟水》记载的“江南第一宅”,不易堂不仅是实体建筑的代称,更成为贯穿文本的核心隐喻,它既是家族命运跌宕的见证者,也是吴地文化传承的活化石,在拆迁危机与产权纠纷中凸显出历史遗产的当代困境。小说通过古画《春日家宴图》的找寻形成叙事线索,展现江南文化传承的复杂肌理。这幅承载家族密码的清代工笔画,在文本中具有双重功能:其物质形态勾连起言耀亭、余白生、老朱等人物跨越世纪的命运关联;其文化意象则暗合苏州园林“移步换景”的美学特征,每个寻访者只能触及真相的局部,如同园林游廊中受限的观景视角,拼图般的叙事策略强化了历史认知的未完成性。管家余白生为追查画作线索背负污名,其子余又继承父志却殒命天灾,邻居老朱穷尽半生搜寻古玩拓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轨迹共同勾画出温润、执着而又坚韧的江南性格图谱。小说在城市化进程与文脉传承的张力间,逐步深入到精神层面展开审思。传统宗族纽带在虚拟社交的侵蚀下日渐脆弱,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遭遇解构危机,不断投射出现代人在现代性进程中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焦虑。通过对文化夹缝中坚守精神原点的市井群像的精心塑造,“不易堂”已然超越地理坐标,成为流动的时代精神符号,小说《不易堂》也从地域性书写升华为人类共通的乡愁寓言。
与《璩家花园》和《不易堂》更多注目城市的变迁发展史不同,胡学文的《龙凤歌》聚焦的是北方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该作品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历史决定论的机械依附,又规避了新历史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过度解构,转而在日常生活的维度寻求重构历史的可能性。在历史书写维度,作者采用“隐形之手”的隐喻策略,将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个体经验编织成互文网络。通过物质匮乏年代的生存困境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症候呈现,以及家长里短对话中的权力关系解构,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个体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化于生存伦理与精神世界的动态建构力量。小说在性别伦理解构方面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龙凤胎兄妹的性别角色倒置,搭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伦理实验场。哥哥朱灯的怯懦与妹妹朱红的强悍,不仅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的既定框架,更揭示了性别规训机制对个体精神世界的禁锢与异化。这种角色错位催生出复杂的心理镜像:朱灯的“恐弱”折射出男性气质焦虑,朱红的“要强”则暗含着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困境。在乡村书写领域,胡学文突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他笔下的乡村既非浪漫化的乌托邦,亦非蒙昧主义的代名词,而是一个交错着人情伦理与权力关系的复杂世界。作者采用“乡下人进城”的经典叙事模式,通过幼弟朱丹的进城务工事故,深入勘探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村中老人讲述的民间传说、艰难生活处境下的精神创伤、奇人异事的口口相传,共同构筑起一个既充满温情、道义又蕴含裂变的乡土世界,完成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深情回望与理性反思,为当代文学的乡土书写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式。
沿海滩涂,作为海洋与陆地漫长博弈的产物,亦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激荡的地理载体,具有鲜明的地理与文化特质。周韫的《海与土》以江苏古长江入海口的滩涂地为故事发生地,将晚清至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风云投射于潮汐涨落的生态图景之中,为生态文学创作贡献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与表达经验。作者以强烈的地域意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生经验,敏锐地将其自然景观与生态系统巧妙地融入叙事之中,使得小说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审美气质。小说以历史与当下交叉的双线叙事结构文本,揭示出历史的厚重与糅杂,展现了生活的变迁与传承。小说语言简明轻快又雅俗共赏,贴近大众而富有韵味;人物个性鲜明,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叙事节奏把握精准,张弛有度,紧张刺激的情节与细腻入微的日常描写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作品不仅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滩涂风物、文化与历史的窗口,更在深层次上引发人们对人类命运、文明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2024年,切入宏大历史进程展开书写的长篇小说还有庄深的《脉》和董红伟的《云边之河》。近七十万字的《脉》以散点透视手法,回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对江南六个家族跌宕发展的命运之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呈现,形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全景,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云边之河》则通过运河边医药世家的无畏抗战事迹,以药师职业伦理为棱镜,将炮制中药材的非遗匠艺、苏北日常生活的纹理融入民族救亡叙事,在烽火中托起文化传承的韧性。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觉醒与青年成长叙事一直是作家群体持续深耕的创作主题,二者共同构成了叩击时代脉搏的双声部,既展现了个体在代际更迭中突破生存困境的坚韧,也映射着社会转型期价值重构的阵痛与新生。
修白的《金缕梅》以三代女性的命运纠葛为叙事主线,在代际冲突与时代变迁的双重语境下,深入探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生命意义的追寻。碧葭与碧苇姐妹的生命轨迹构成了现代女性的双重镜像:碧葭从爱情幻灭到西藏支教的人生轨迹,完成了从“被拯救者”到“拯救者”的蜕变,象征着女性从依附走向自立的觉醒历程;碧苇则以传统利他主义者的形象,在平凡中诠释存在的价值,展现了另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而碧葭之女小乖跨越国界,投身动保组织的自我实现,不仅是对个体价值的追寻,更折射出全球化视野下女性意识的升华,即从家庭伦理的桎梏中突围,以世界性的担当重构生命意义。作者以“金缕梅”为核心隐喻,既暗示女性如忍冬般隐忍的生存境遇,又赋予其破茧重生的生命力。
褚婷的《重影》则以锐利精准的笔触剖开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叙事中,织就一张密布现实痛感的网。小说以主人公柯苗的双城通勤为明线,勾连起婚姻、疾病、原生家庭等暗线,将“重影”这一意象升华为女性生命经验的隐喻,既是生理病症的模糊,也是身份割裂的混沌,更是理想与现实交叠的迷惘。作者通过“既不幸福也不悲惨”的中性书写,精准捕捉到当代婚姻关系的异化本质。小说还重点刻画了几位面临不同生活困境的女性人物形象,描绘出当代都市女性在家庭伦理、职场规则、代际冲突中的精神群像。小说始终贯穿着女性之间互为镜像的精神照拂与生存智慧,这种超越功利性的情感纽带,构成了抵御现实困境的温暖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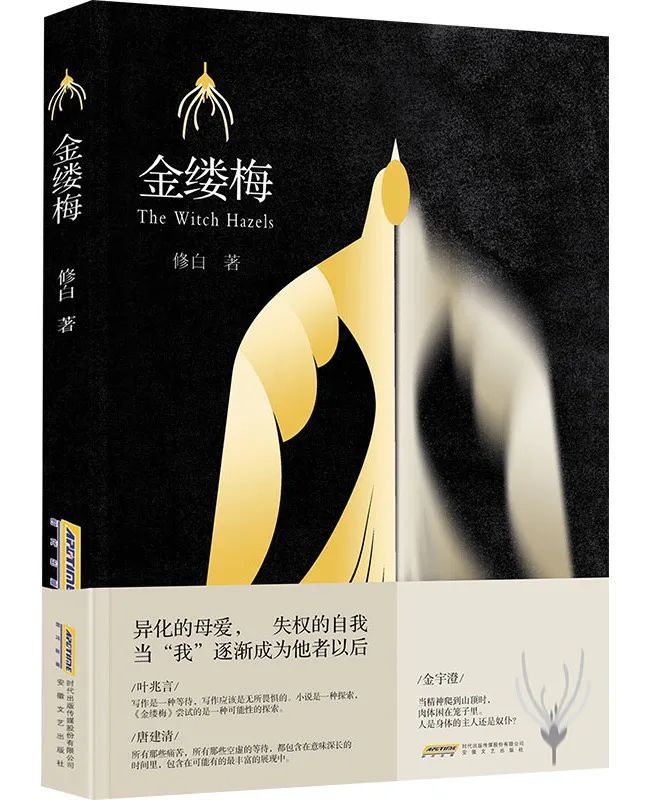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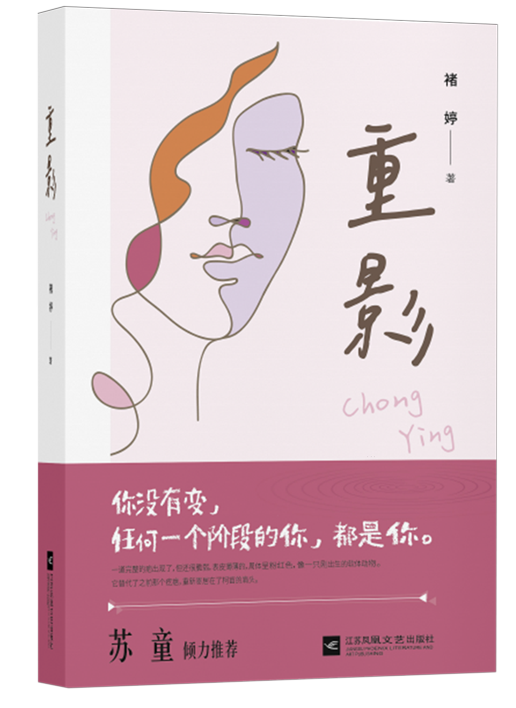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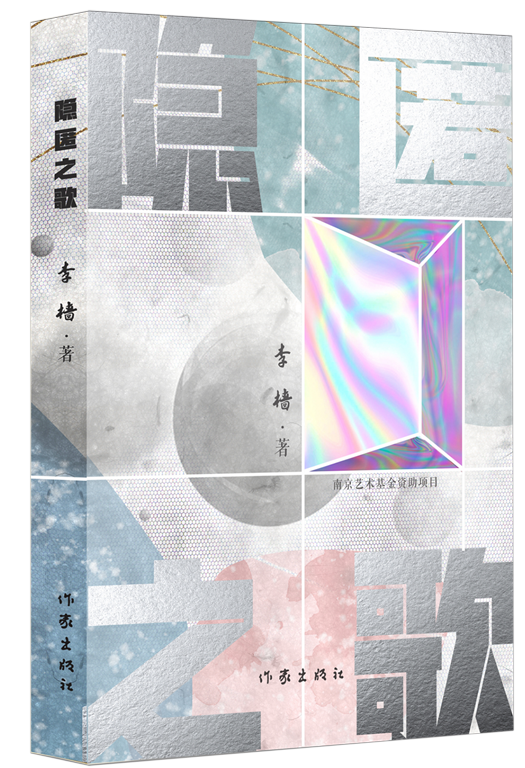
李樯的《隐匿之歌》以心理学视角切入当代青年男女的精神困境,通过两对人物青春、友情、亲情、婚姻所构成的成长叙事,揭示了物质丰裕时代青年隐秘的心理危机与救赎希望。小说原名《栅栏》,既象征着个体为自我保护构筑的心理防线,也暗喻其可能演变为阻碍自我认知与内洽和解的桎梏。作者以第一、三人称视角交替开展叙述,融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荣格“阴影整合”理论,通过梦境、创伤记忆与代际心理传递,剖析原生家庭对人格的深层影响,并将当代青年复杂的内心处境置于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语境中进行观察与审视。作品结构紧密、贴合日常,鲜明的在场感与画面感以及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情节设计,带来极强的可读性。小说既是对现代社会青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深度扫描,也以文学叙事探索精神疗愈的可能性,为文学介入心理健康议题开辟了新路径。
姜琍敏的《独上高楼》、龙景天的《月蚀》、王顺法的《看夜空的人》,共同编织成不同世代青年的成长启示录。《独上高楼》以知青生活为底色,将主人公许硕从下放工人蜕变为作家的历程,凝练为一代青年理想主义的缩影。他效仿马丁·伊登式的苦行,以文学为救赎,在省报零星诗作中埋下火种,最终借中长篇小说的燎原之势叩开文学圣殿。作者并未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为粗粝现实注入诗意哲思,揭示“生存即凯歌”的平民英雄主义。
《月蚀》以群体叙事展开,篮球场上的对抗与场外的人生博弈形成镜像,竞技体育的胜负哲学在此升华为对坚强生命的赞颂。小说结构繁复而不失精巧,拼贴出少年们被命运撕裂又自愈的成长轨迹,展现出青春的芜杂面貌。作品不仅描绘了篮球场上的热血与激情,更深入探讨了少年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自我认知的冲突,这种将个体创伤升华为集体共鸣的叙事野心,使作品具备了超越一般青春文学的审美力量。
《看夜空的人》以宜城青年企业家苏南带领家族企业突围的故事,生动展现民营企业在时代浪潮中的兴衰起伏,也写就了一代人在父辈功业基础上,重新探寻人生路向的时代新章。主人公苏南从海外精英到临危受命的“太子”,身份的急转揭开守旧与创新交锋的序幕。小说以曲折跌宕的情节,入木三分地刻写出家族企业盘根错节的亲缘网络与现代化转型的深层冲突。作者深刻解剖传统民企的生存逻辑,尤其是对“人情社会”与“契约精神”之间激烈拉锯的精彩描写,为文本赋予了强烈的现实穿透力。
新旧之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当全球化浪潮不断冲刷传统文化的生存土壤,非遗技艺作为民族精神基因的活化载体,其存续问题已然演化为如何重构文化认同、唤醒集体记忆的时代命题。钱庄的《裱画师》与宋娃的《桃艺》,皆以“器物载道”,裱画的接缝处暗藏人性善恶的纹理,桃核的方寸间刻绘文化传承的密码,共同描绘出传统技艺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景象,在展现传统手艺人在物质诱惑下的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彰显了文学对文化根脉守护的自觉担当。
《裱画师》以一场徐渭水墨杂花长卷的拍卖风波为引,编织出一幅艺术与人性交错的浮世绘。小说通过记者胡总的视角,揭开裱画师秋尘的隐秘人生与书画江湖的暗流涌动。旧裱与新裱的更迭、真品与赝品的争议、利益与情义的撕扯,构成叙事的核心张力,既是对艺术本质的叩问,也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剖析。秋尘作为非遗裱画师,以“赝品”断言搅动风云,实则是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也是对资本侵略的无声反抗。这位聋哑裱画师身世坎坷,幼年失声、家族凋零,却在装裱技艺中寄托了对传统的敬畏。他的“赝品”指控,既是技术判断,更暗含道德审判,画作承载的并非徐渭的魂,而是权力与贪欲的污迹。秋尘生理的沉默与艺术表达的滔滔不绝形成矛盾式存在,暗示着艺术家在世俗社会中的失语困境,亦成为对抗喧嚣世界的武器,其孤傲背后是对艺术本真的执着。
《桃艺》以非遗桃核雕刻为叙事载体,在传统手工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浮刻出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人性张力的现实世界。作品以张根的技艺传承与情感纠葛为主线,将非遗保护的时代命题与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相结合,深刻探讨了当代手艺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坚守,展现出作者对文化根脉与人性深度的双重关注。主人公张根与李桃香、吴琼的情感纠葛,绝非简单的三角恋叙事,而是通过阶层壁垒、商业资本与传统文化的对峙,构建起多个向度的人性考场。作品以扎实的细节与克制的抒情,为当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深邃的力量,也印证了江苏青年作家对纯文学创作的真诚与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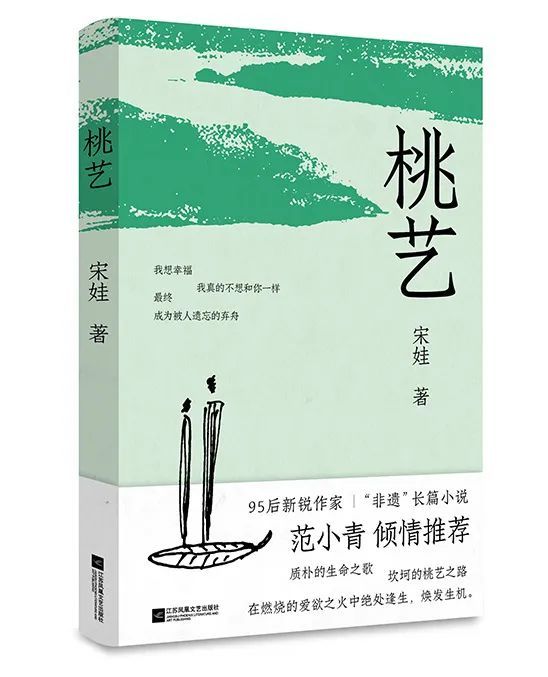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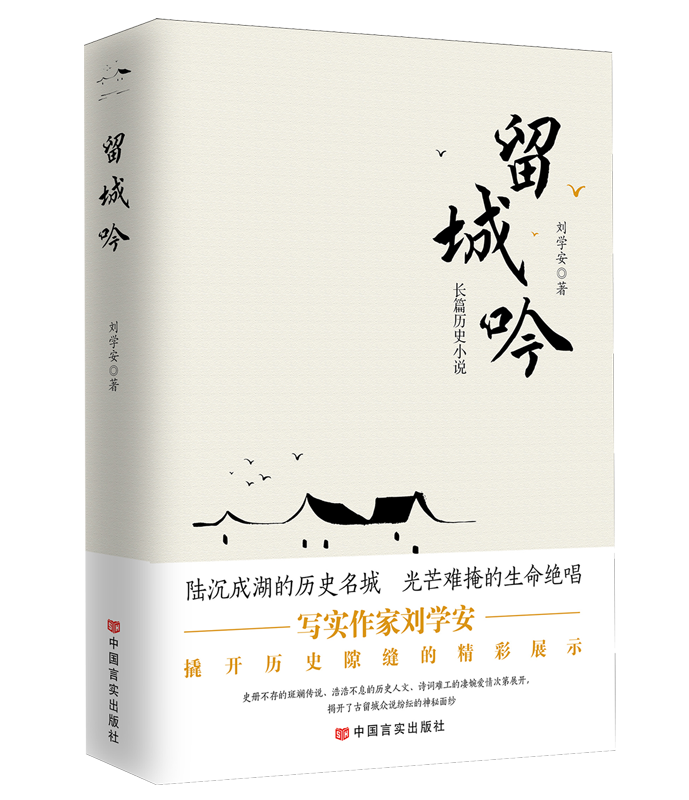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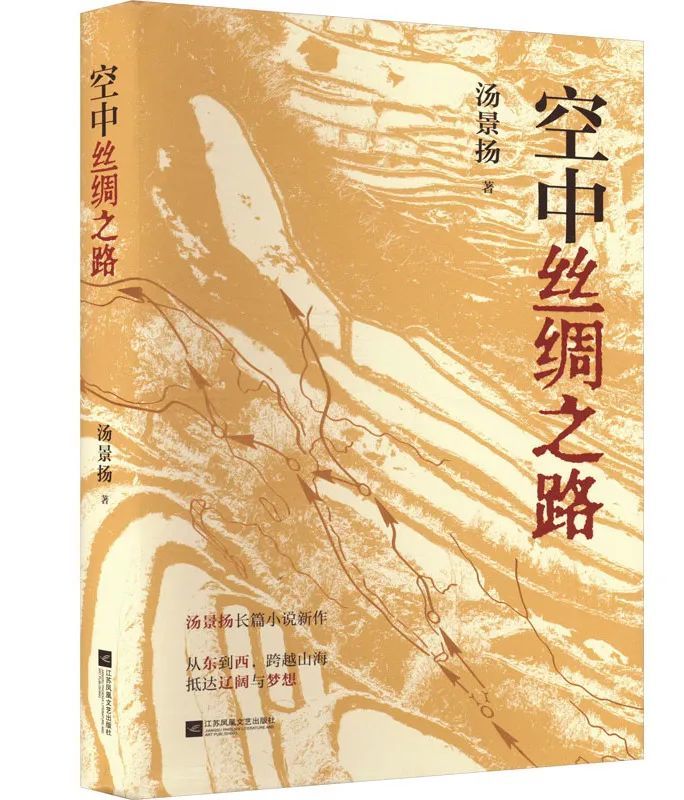
江苏大地上,开拓者的跫音始终回荡,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奋斗者们,一直是江苏作家笔耕不辍的创作对象。刘学安的《留城吟》与汤景扬的《空中丝绸之路》,在历史烟霭与现代潮声的隔空对话中,连缀出建设者们贯通古今的精神脉络。长篇历史小说《留城吟》,通过明万历年间张良后人张谦“兴城旺寺”的壮举,再现了江苏沛县古留城这座陆沉古城的辉煌与悲歌。作品以家族、寺庙、学堂为叙事支点,串联起张氏后人复兴留城的理想与行动,勾勒出明末清初留城的风俗人情与历史人文景观。小说以原创诗词、古典意象等元素,赋予文本雅致含蓄的审美特质。作品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深情书写和致敬,也为地方文化传承与地域文学创新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空中丝绸之路》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新时代援疆事业的壮阔诗篇。小说聚焦教育振兴、产业扶贫等民生议题,塑造了一群扎根边疆的奋斗者形象。他们不完美却真实,在事业与情感的抉择中彰显出质朴的责任感。从黄海之滨到中哈边境,作者通过商战博弈、文化交融等情节,揭示东西部资源互补的深层逻辑,更借民族融合的细节,诠释和传递了现代丝路精神。
总体而言,2024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题材多元、风格多样、写法丰富的蓬勃发展面貌。老中青三代作家齐头并进、携手创新,文学苏军以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自觉,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展现出直面社会问题的责任担当,通过生动的艺术实践为新时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贡献了具有标识意义的江苏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