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阅读史;父亲形象;南方想象;《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
2024年3月,《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向迅的首部小说集。在此之前,向迅出版有《谁还能衣锦还乡》《声音博物馆》《与父亲书》等多部散文集,接连获得林语堂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等多项荣誉,《与父亲书》斩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论及该小说集的创作缘起,或可追溯到2019年的冬夜,在赶回鲁迅文学院十里堡校区时,向迅受到周明全的邀约,在其主编的《大家》杂志开设专栏。按照专栏常例与周明全的建议,专栏初步拟定为“六篇同一主题的散文”,并由向迅敲定名称为“镜中迷宫”。意外的是,在交稿日期截止前,困于琐事的向迅“迟迟拿不出稿子”,只好将藏于屉中的短篇小说《小镇艺术家》拿出来“江湖救急”,正是这一举动,“无意间把散文专栏变成了小说专栏”。收入专栏的六篇小说《小镇艺术家》《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父亲失踪史》《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白色灯塔》《悬置地带》,加上分别发表在《芙蓉》和《山花》上的《妻子变形记》与《七月晚餐》,共同组成了这部小说集。值得注意的是,在向迅的小说处女作《小镇艺术家》发表之前,散文《H先生》已被《黄河文学》当作小说发表于2019年第11期,而为向迅偏爱的短篇小说《七月晚餐》却被当成散文发表,“还被收入一个散文年选”。如何看待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成为向迅在创作转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进一步看,由散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向迅作了哪些尝试和改变?过往的书写经验,在跨文体实验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正是本文试图思考和探索的,而其中蕴含的方法和手段,同样为后来者的创作转向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径与法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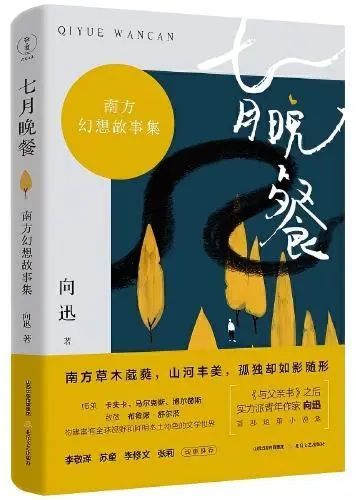
《七月晚餐》,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4年版
一、阅读史与文学创作的原点
“我们永远无法精确知道自己所学何物、所忘何物、所记得的又是什么。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阅读活动拯救了那么多过去的声音,有时候还可以好好地将它们保存到未来,届时我们或许还会以大胆与出乎意料的方式来运用它们。”阅读是写作的原点,写作是阅读的深化,无论是在散文写作还是小说创作中,作者都会或有意或无意地将阅读体会和感受融入其中,特别是在有着明确阅读兴趣和判断的向迅身上,既有的个人阅读史成为其文学作品中的关键一环,也成为理解其散文与小说写作的重要角度。
需要指出的是,向迅的散文写作以记人叙事为主,多描绘个体成长、亲朋往事和乡土情感,并非侧重知识文化讲述的学者散文,文艺作品在文中的出现,主要体现为思绪延展过程中的一笔带过,如《镜子》提到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德语课》、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廊桥遗梦》和安德雷斯·拜斯(Andrés Baiz)导演《黑暗面》,《姓李的树》谈及卢梅坡《雪梅》、曹雪芹《红楼梦》,《乡村安魂曲》说起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低地》等。在《寂静的时刻》中,向迅谈到对于经典之作的阅读和咀嚼,“远远比闭门造车的写作更让人安静,也远远比一场大雪更让人清醒”。从列举到的《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追忆似水年华》《一粒麦种》等作品中,也可见出向迅对于先锋文学资源的吸收,而这在其小说创作中有更为突出的显现。个别幻想篇章和行旅散记,则体现出向迅对于书籍和知识背景的深入体察,阅读史成为支撑内容开展的框架,如刘勰《文心雕龙》之于《大树》、朱自清《绿》《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之于《瓯海踪迹》,彰显出向迅在文化散文创作领域的无限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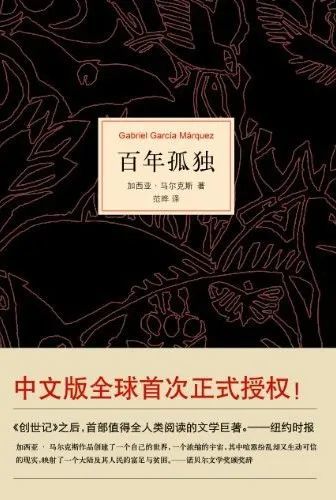
《百年孤独》,
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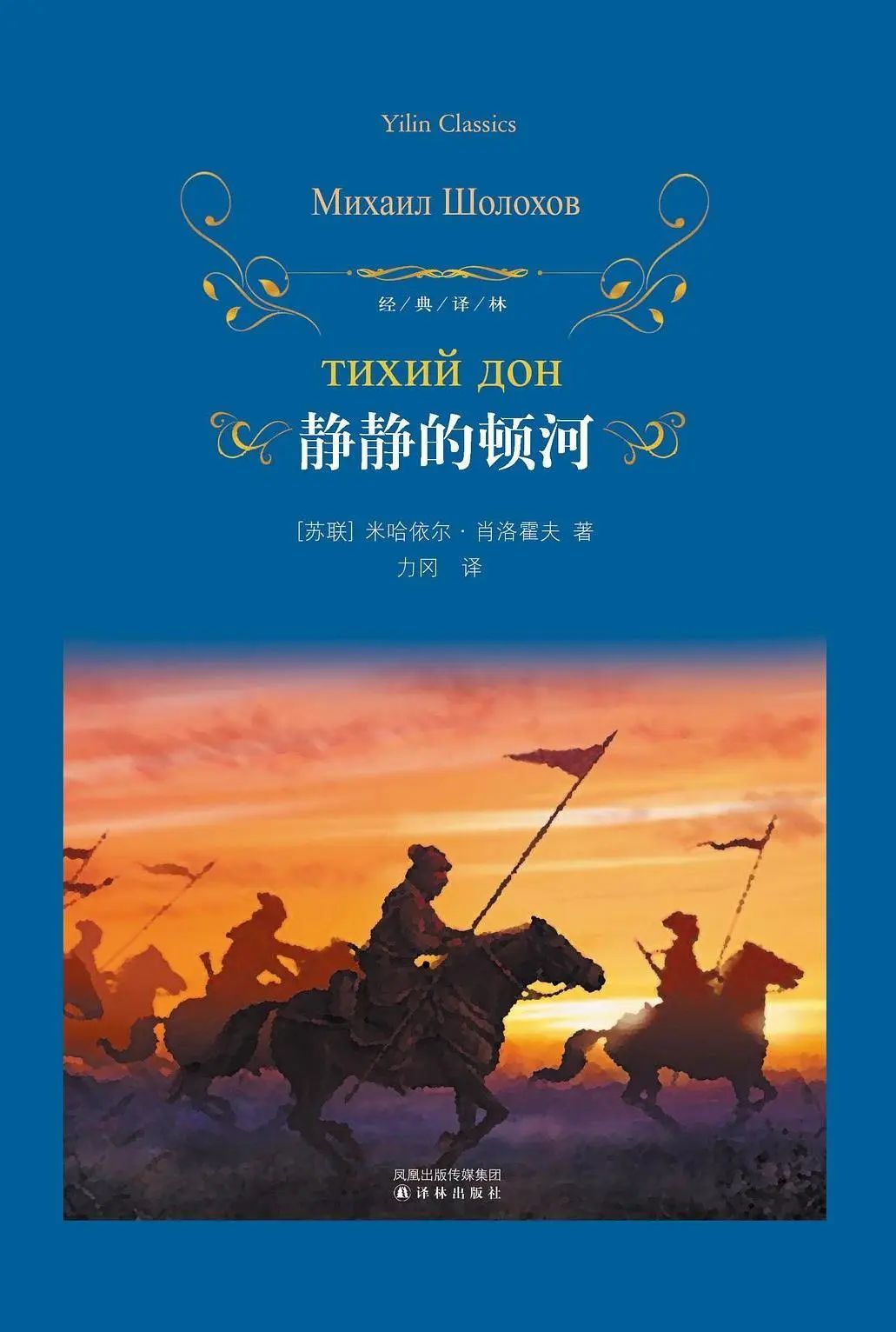
《静静的顿河》,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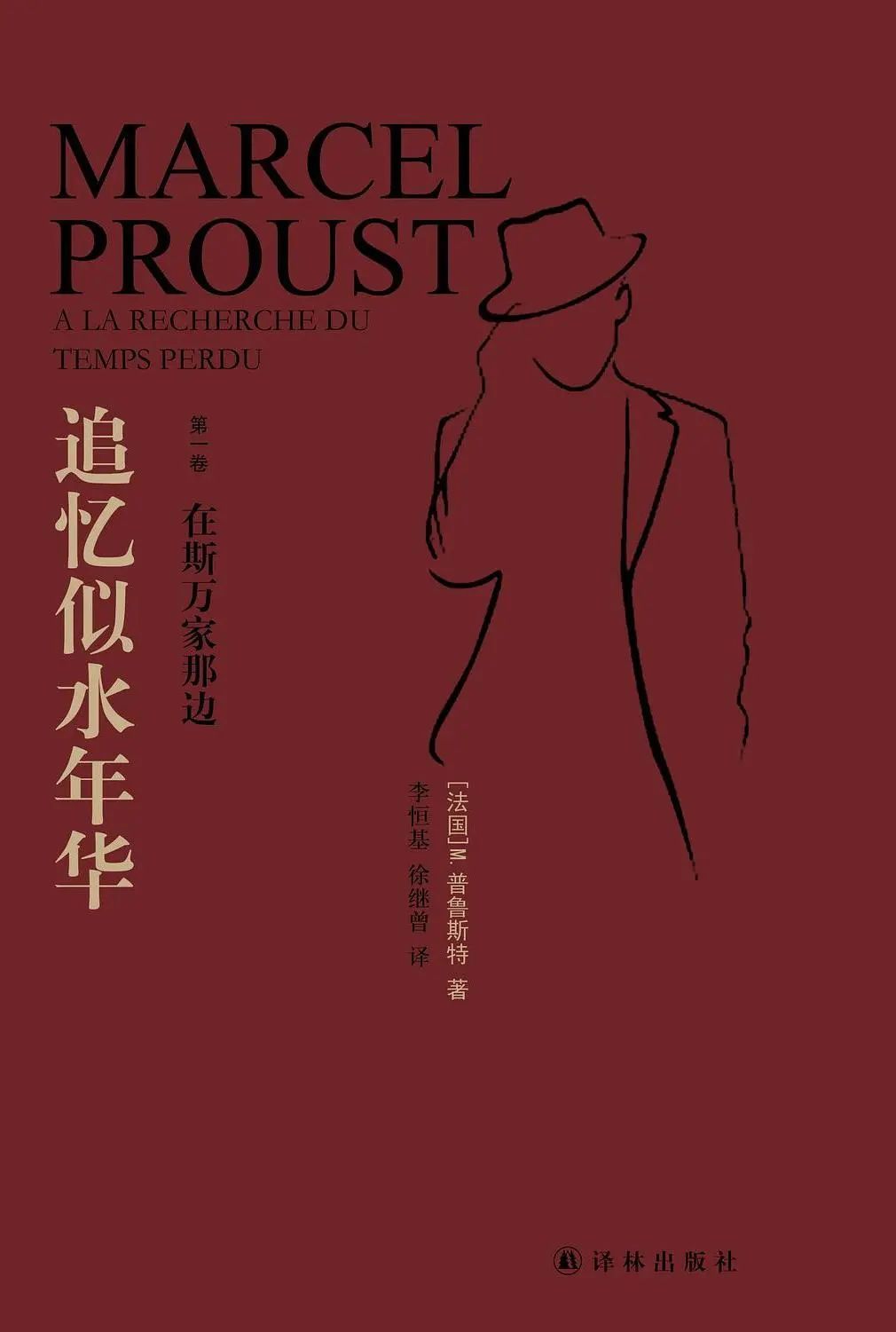
《追忆似水年华》,
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相较而言,小说写作与个体阅读史的关系更为复杂,这在向迅的《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中,集中表现为书籍作为故事发展的道具而存在、经典文本成为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致敬对象,以及小说对于经典之作的戏仿等情况。在这其中,作为道具存在的文学文本,更多是出于叙事的需要而被合理使用,与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深层意蕴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小镇艺术家》中卡夫卡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成为见证“我”穿梭于梦境和现实的关键物品,“我”与中年男人的对话由《饥饿艺术家》开启,并过渡到对于小镇出现的艺术家的讨论,这可视为“我”进入梦乡的伊始;而结尾处躺在角落里的“封面上多了好些个瓜子壳”的《饥饿艺术家》,将“我”从迷糊茫然的幻境中拉出。《父亲失踪史》中,蒲松龄《崂山道士》和马歇尔·埃梅(Marcel Aymé)《穿墙人》也是作为知识的补充,目的是让小说叙述的关于父亲失踪的故事更为可信,为此向迅还专门虚构了并不存在的“韩国学者朴尚文先生编选,南京外国语大学柳鸣教授翻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亚洲穿墙术故事集》。
向迅小说对于经典文本的借鉴和致意,仅从标题上就可见出,如《巨翅老人》之于《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沙之书》之于《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等,而经典文本更进一步的影响,是让向迅找到写作的起点,并以此来构思作品。《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这篇小说“写得畅快,几无障碍”“自从读过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之后,那个故事好似就在我心底扎下了根”,向迅将巨翅老人的故事融入小说中的秃头老人的梦中,探究小说与梦境的关系,这在某种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所营造的现实与幻想交织的魔幻世界的承继。《沙之书》收入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75年发表的小说集,其中那本虚构的“沙之书”象征着无穷无尽,这样的理念实际上脱胎于《小径分岔的花园》,指向“时间分岔”的概念,而向迅在《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中尝试的,正是创作一种可以永远写下去的小说。小说中提及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所创作的作品“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同一句话,无限重复的一句话”,向迅反其道而行之,从第二章起,每一章的前两句话都是无限重复的:“我想到父亲。一个夏日的清晨,他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梦见了一座比魔鬼还要奇怪的花园。”在阅读《妻子变形记》的过程中,卡夫卡(Franz Kafka)的《变形记》成为相对照的叙事背景。“戏仿除了作为外部读者的接受对象,在建立过程中还可以利用想象读者或接受者的期待。”卡夫卡站在变为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视角上,写出现代社会的“异化”与“孤独”,向迅沿着卡夫卡的思考拓展,对准卡夫卡《变形记》百年阅读史中为人忽略的推销员家人的内心情况,将视线聚焦于面对妻子变成猪的“我”,通过“我”的慌乱、挣扎与痛苦,探究荒诞与残酷背后的合理和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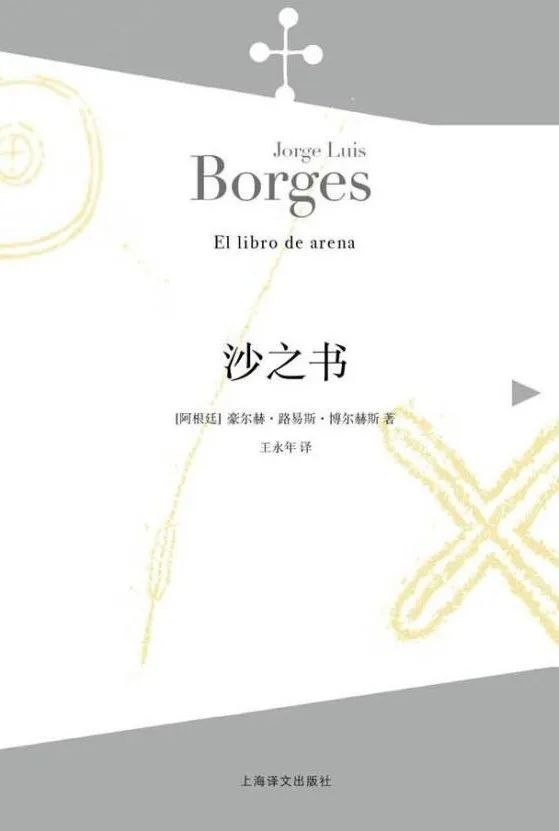
《沙之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变形记》,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向迅散文创作中出现文艺作品,契合于发散式的写作和思维方式,更多是一种基于联想的漫谈,而其中透露出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偏好,在其小说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体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以多样化的方式出现在向迅构建的文本中,那些经典作品发挥着推进情节发展、提供创作灵感和形成互文对照等作用,帮助我们打开《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的内部空间。“我们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文本所具有的文学性,而是文学式的阅读方式。”从某种角度上看,阅读史在创作中的彰显,在影响创作者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和思考方向。
二、父亲形象与小说、散文的界限
在《与父亲书》的后记中,向迅自陈当他将最后一期稿件发给《大家》编辑时,“吃惊地发现,六篇小说中,有五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拥有一个身份,那即是父亲”,这五篇小说分别是《小镇艺术家》《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父亲失踪史》《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白色灯塔》,加上那篇由“关于父亲的长文”中“单独拎出来”的《七月晚餐》,小说集《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中的八篇小说,其中四分之三都与父亲相关。“父亲”这一文化形象,同样也是向迅在散文中反复书写和描绘的,散文集《声音博物馆》中的《南方故事集》《父与子》《消失的原野》《雕刻时间的人》《漫长的等待》等,都在讲述父亲的过往和父子的相处,而散文集《与父亲书》更是“写给父亲的书,献给父亲的书”,可以直接“看成是一封写给父亲的长信”。“父亲”像是“一口创作的深井”,滋润着向迅的写作,而其在不同文体中对于“父亲”的塑造和阐发,体现出其对于小说与散文界限的认知和理解。
在《与父亲书》的写作过程中,向迅试图刻画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性格的父亲”。《鼠患之年》中的父亲壮年有力,勇斗大蛇,却也困于贫苦生活;《九月永存》与《独角兽》中的父亲走向晚年,为疾病折磨,变成了一只“需要独自面对一切未知事情的独角兽”;《巴别塔》中的父亲逐渐步入中年,与母亲维持着脆弱的婚姻关系,深陷情感野史的风波之中;《时间城堡》回首父亲的青少年时期,不为祖父母所爱,“像个孤儿”。与此相区别的是,向迅在小说集中详细展开书写的是“失踪的父亲,作为失败者的父亲”。《小镇艺术家》中的音乐家面对妻子离世、女儿远离、指挥遭到戏弄的多重打击,突然在小镇失踪,“好像从人间消失了”;《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中的堂祖父沉溺于生出巨大翅膀的梦境多年,与家人关系恶化,离奇失踪,在厢房内的工作间里留下的“一对巨大而又轻盈的翅膀”也被妻子砸毁;《父亲失踪史》中身患重疾的父亲在六月中旬的傍晚不翼而飞,而“我”在父亲留下的破损的日记簿中看到了关于穿墙术的记录;《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中“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建筑师,他一直被繁琐的家事所捆绑,而那试图建造空中花园的梦想,长期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初具雏形的花园也在他离世后成了鸡圈;《白色灯塔》中的父亲托人带回要去明月岛办事的口信,留下被流言蜚语击垮的母亲和家人,而“我”在十年后踏上寻找父亲之路,却在明月岛上迷失于有关白色灯塔的传闻,“跳进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之中”。写作散文时,向迅的追求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饰的父亲,如实地写进文章里”,展现的是父亲各个年龄段的不同情况,还原复杂多变的真实的父亲形象;而在小说中,向迅聚焦于失败者与失踪者形象,选取冲突性更强的讲述方式,吸收借鉴先锋文学的现代派技法,通过夸张、变形、荒诞等艺术表现方法,表现父亲的孤独、痛苦和逃离。透过其具象化的父亲叙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人共通的悲剧命运和生命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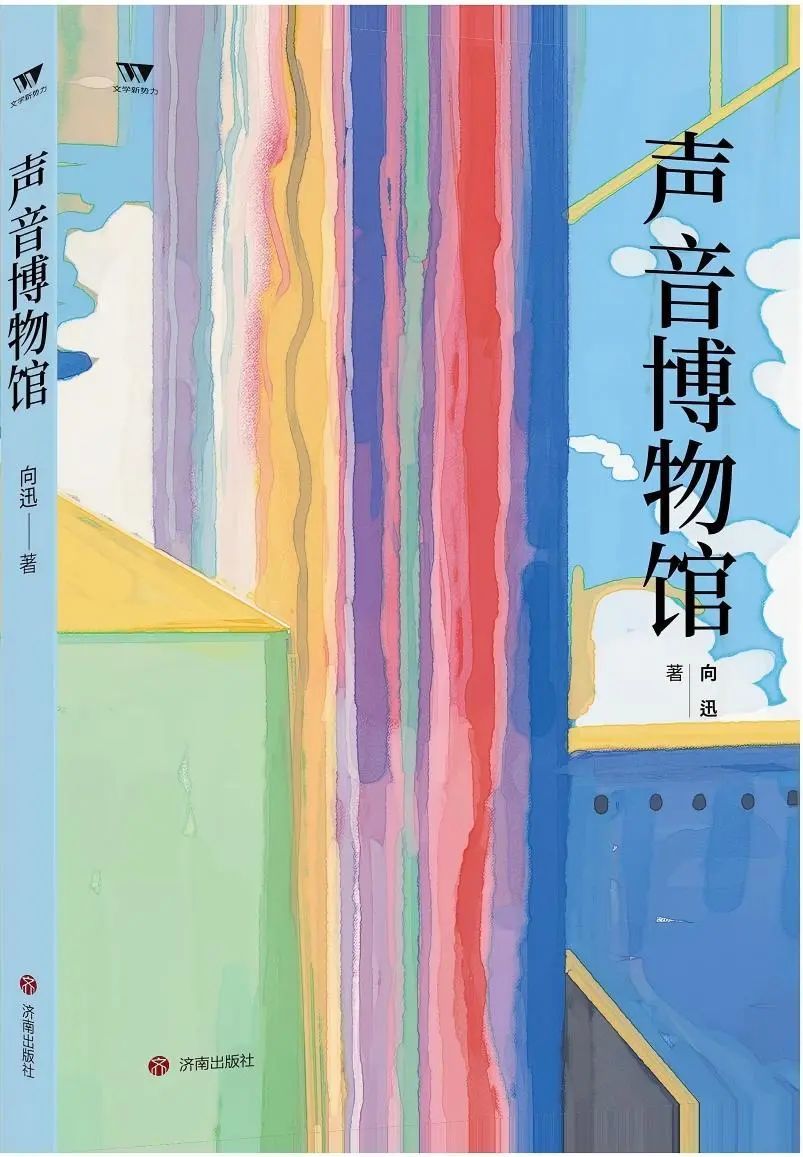
《声音博物馆》,济南出版社2024年版
《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中关于父亲的篇目,诸多细节与散文相对应,或有意或无意地“激发读者更多的想象和知识”,让人产生小说从散文的枝节中生长而出的感觉。《七月晚餐》对于父亲勇斗大蛇的描绘,令读者不自觉联想起《鼠患之年》中父亲捉蛇的场景,特别是两者中有关“我”抓住蛇身的叙述,形成极具感官刺激的互文对照。在此之外,《鼠患之年》第五节开篇的几句话,“三月的时候,父亲身上长满了隐形的羽毛,还有一对巨大的翅膀”,与《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遥相呼应;而“他要出远门了。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和《白色灯塔》开篇“父亲托人捎回一个口信:他到一个叫明月岛的地方办事去了,让我们在家里等他”之间,也有隐约可见的熟悉感。《雕刻时间的人》和《漫长的等待》中的父亲手艺精湛,深受村民尊重,却陷在养家糊口的困苦之中,跟承担生存压力的祖父一样,“在年轻时,肯定也是怀有一腔抱负的,只不过被做父亲的责任感击破了”,这与《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中的父亲所面临的窘境何其相似。
需要注意的是,向迅小说并非对其散文的续写,而是在互文之外有着全新的开拓,两者就像是两条相交的曲线,交集重合后向不同方向延展。《七月晚餐》以父亲抓蛇烹蛇为重心,透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横截面,描绘了父亲的勇猛和家庭的温馨;而清除家中之蛇只是《鼠患之年》的一个插曲,文章着重刻画的是父亲与家人的多年相处,纵向深入地展露父子关系与家庭生活。《鼠患之年》中以翅膀隐喻父亲离家工作,同时以此象征父亲的理想与抱负,而在父亲无法带回学费,到处借钱筹措时,“身上的羽毛不见了,那对巨大的翅膀也不见了”。《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中的巨大翅膀则是老人梦中的存在,借此探讨的是小说与梦境的关联。而在共同的失意者形象之外,《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以在梦中建造空中花园的方式,借由魔幻的叙事找到了安放父亲梦想的位置,并通过无限循环的讲述方式,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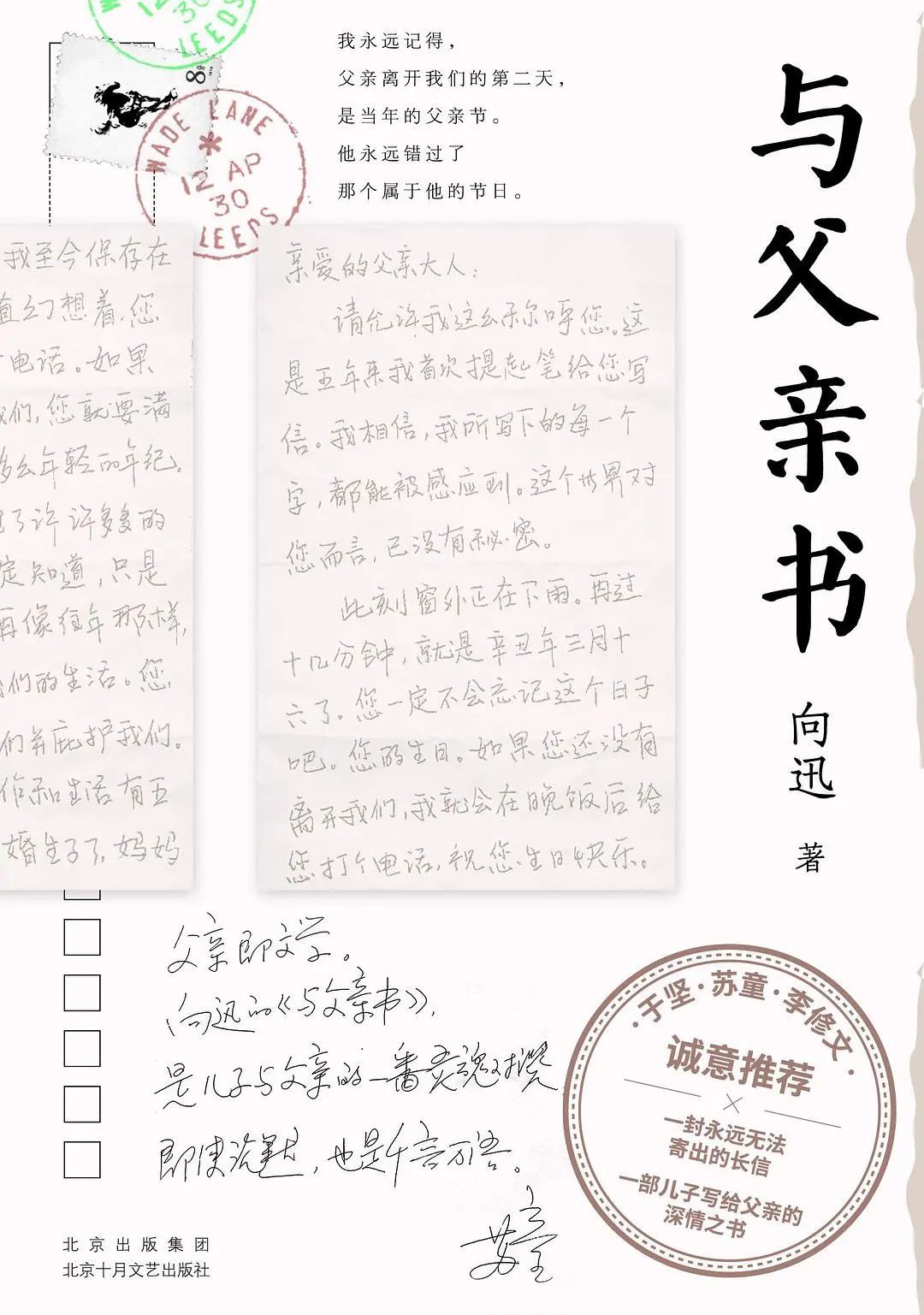
《与父亲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版
《白色灯塔》见刊不久,向迅收到“一位浙江老先生的来信,说读了这篇文章颇为感动云云”,向迅猜测老先生是将小说读成了散文,“把原本子虚乌有之事当成了我的亲身经历”。而对于《七月晚餐》被当成散文的情况,向迅指出开头和结尾虚构属性较强,中间部分则将“父亲和哥哥两个人所做的事情,合并到了父亲身上”,如此看来,似乎虚构与否,成了判定文体的密钥所在。矛盾之处在于,向迅似乎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提出“这好像也不是把它划归为小说的理由”,并直言无法给出这篇作品的文体归属的答案。事实上,向迅并不欣赏“长得特别像散文的散文和以讲故事为核心的小说”,而这样的创作背后正是基于以虚构/非虚构作为划分小说/散文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向迅意识到简单以虚构与否划定文体的局限性,但在进行作品发表和编集时,又不得不以此为武器捍卫自我判定的合法性。又或许,散文中有虚构一面,小说中有真实一面,关键在于创作者以怎样的方式去讲述,它们更多的不同来自于语言和思维方式,而这才是“散文作者转型写小说”的最大困难,也是向迅努力尝试和改变的重要方面。
三、南方想象与艺术气韵的生成
以“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为小说集命名,在向迅看来,是因为《七月晚餐》是“最不像小说的那一篇”,契合自己对于小说创作的理解,故而他放弃了更能够概括作品集主题内容的《父亲失踪史》。而加上“南方幻想故事集”,则是“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于潮湿的南方,而且每一个都带有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色彩”。质言之,《七月晚餐》为向迅所偏爱,而“南方幻想”是对小说集整体气韵的凝练表达,两者代表了向迅的创作追求和写作风格,共同支撑起了小说集的灵魂。
小说集以同名短篇《七月晚餐》为起首,作品开篇即展开的对于潮湿南方的描述,“七月在黄昏时分进驻村子,携带着一场强劲雨水。空气潮湿而又燠热,扑朔着蜀葵隐忍的花香和浓郁的泥腥气”,某种角度上或可视为对整部作品集背景的交代。《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中“我”与父亲拜访堂祖父时,正是镇上最好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温软而又略微含有一点甜酒味的气息”。此外,《小镇艺术家》中点明,火车是行驶在长沙到岳阳的途中,而“我”却坠入到与中年男人在无名火车站的圆形广场上交谈的梦境里。《悬置地带》中的A来自南方,“从小到大从未见识过真正的雪”,决定在元旦时候来到“我”所在的北方城市。令人困惑的是,在作品集的其他篇目中,并未有对故事发生于南方的明确表述,更没有对环境潮湿的描述,甚至出现“阳光炫目,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击中了我”的场景。
容易为人忽略的是,向迅写作《小镇艺术家》时,也即从事小说写作的开始,是在2019年8月,当时正是“南方冒火的八月,不知怎的就技痒难耐,想动手写一篇幻想小说,而且真的写起来了”。而这也就指向了南方在潮湿之外的另一种气候,那就是夏日的酷热。可以说,潮湿与闷热,本就是南方夏季的一体两面。而小说集中的其他篇章,多以时间脉络暗示了故事发生的时节:《父亲失踪史》中的父亲失踪在“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又在四年后一个滚烫的中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中的父亲是在夏日的清晨告诉“我”,他梦到了奇怪的花园,并生出建造空中花园的愿望;《妻子变形记》中的“我”在“七月的一个清晨”从“深如沼泽的梦中醒来”,发现妻子变成了一头“浑身焕发着银质光泽的猪”。从这个角度来看,同名短篇《七月晚餐》对于环境背景的设定和发生时间的明确,使得它成为解开向迅所设置的故事发生于潮湿南方的关键线索,拥有不同于其他篇目的整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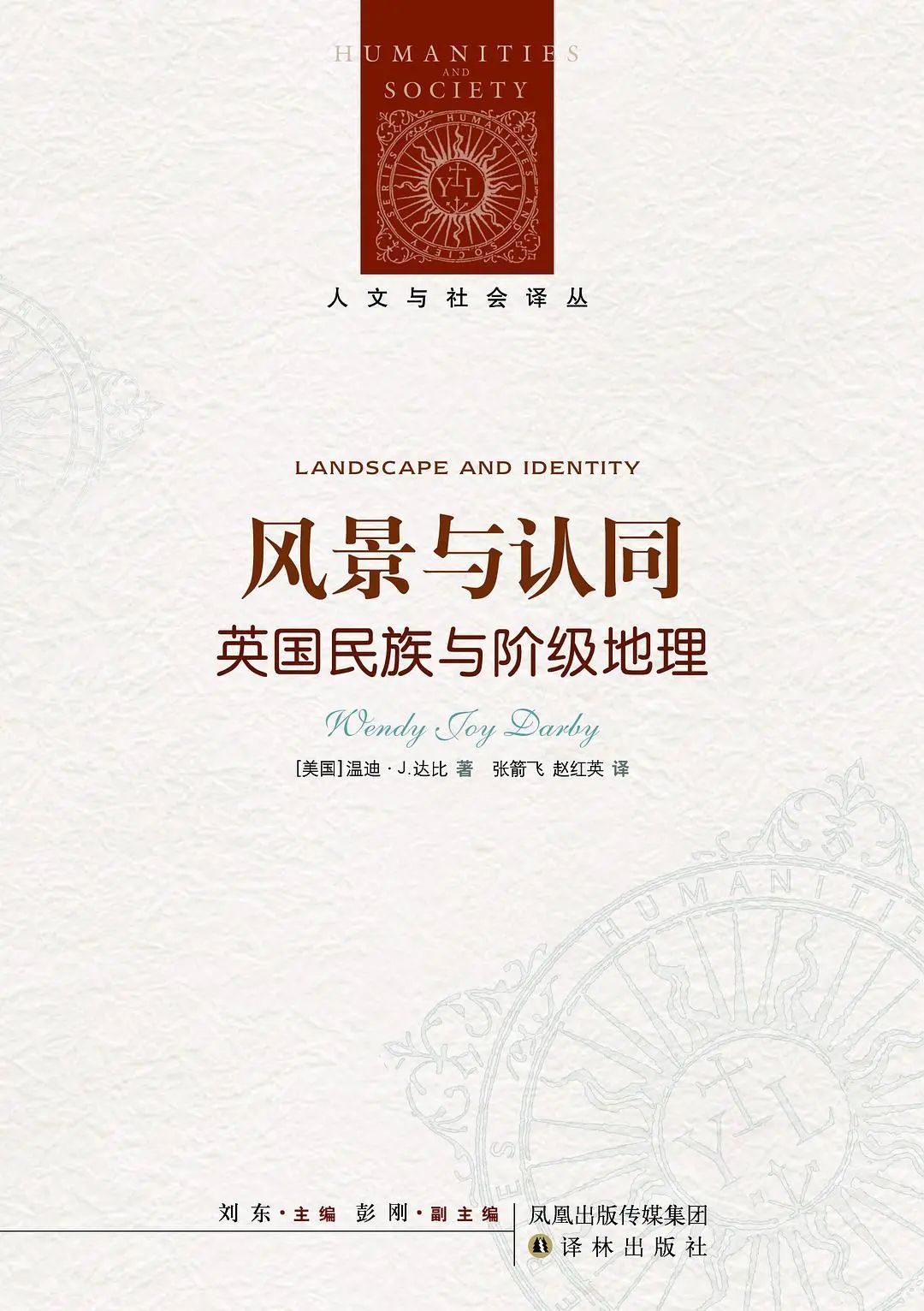
《风景与认同》,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除却故事背景的设立,小说集的南方气质还体现在作品的语言和人物的性格等层面。水汽氤氲的南方,气候湿润,地形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向迅生长的鄂西,多山地丘陵,河流纵横交错,山峦起伏不定。“风景与语言的联系通过地名的记忆和隔绝状态得以保持”,与南方环境相契合的是,向迅在创作中偏向使用湿润绵柔的语言,以细腻的笔触进行故事的讲述,而这也和他的散文写作风格相一致。通过多部作品塑造的父亲形象,展现出相对统一的内敛、温和、务实、家庭观念重等性格特征,这同样也是向迅在《与父亲书》等散文集中所刻画的父亲形象身上所体现出的特质。以此观之,向迅在散文和小说写作中表现出的南方韵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不容忽视的是,在向迅的小说和创作谈中,都有着苏童的身影。如《妻子变形记》中的“我”回想与妻子的第一次相遇,当时她坐在长椅上,手上捧着的是苏童的短篇小说集《十九间房》。而苏童在与弟子们聚会期间提到的“故事到契诃夫为止”的观点,深深影响到了向迅对于文学写作的认识,作品需要为“读者带来文本之外的思考”“给同行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的方法”,这也是向迅想要写出跨越文体界限风格的小说和散文的重要原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向迅,求学时期的导师正是苏童,在与笔者的对谈中,向迅坦言读过苏童的大量小说、散文和创作谈,很难不受到苏童的影响,而研究者在阐发苏童作品时所引入的“南方诗学”“南方叙事”“南方精神”“南方意象”等视角,让苏童逐渐成为“南方想象”的代言人,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向迅的创作,为向迅的南方写作提供源源不绝的养料。

《南方想象的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先行者,苏童充分吸收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卡夫卡等人的写作资源,而这也是向迅所阅读和借鉴的,正如李修文在《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推荐语中所精准把握到的,向迅的小说中“携带着先锋文学的遗风”,这在小说集中弥漫着的博尔赫斯式的幻想色彩中得到完美展现。从某种意义上看,苏童的文学写作,成为认识向迅将“南方”和“幻想”结合起来的一个切口,而这两种元素对于填充小说的枝干和血肉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是向迅将“南方幻想故事集”作为小说集副标题的原因所在。
结语
文学编辑有两栖型和专职型之分,“两栖型兼顾写作与编辑,专职型全身心从事编辑工作”,向迅承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陈独秀、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实践的兼顾写作与编辑的传统,并在《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中实现了由散文过渡到小说的创作转型。在向迅的创作中,小说与散文相辅相成,散文为小说创作提供生长点,同时成为认识小说创作的重要角度;小说延续并拓宽着散文的思考,创造出多元丰富且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世界。换个角度看,或许向迅试图通过跨文体写作回到中国的文章传统,打破固有的小说与散文的二元对立认知,写出难以被轻易界定文体、边界相对模糊的文学作品,而不只是小说与散文,这也是向迅想要写出不像散文的散文和不似小说的小说的因由所在。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向迅通过《与父亲书》和《七月晚餐:南方幻想故事集》共同构建出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父亲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以散文《父亲的病》讽刺庸医误人,以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讨论怎样改革家庭;朱自清用散文《背影》写出父亲的关怀与爱护;老舍借《二马》中的老马揭示了保守顽固的旧文化理念;而巴金的《家》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则通过父亲形象的塑造窥视封建大家族的落后腐朽。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汪曾祺以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倡导平等温馨的父子关系;梁晓声通过散文集《致父亲》写出父亲的专制和父爱的伟大;张洁用《无字》中对精神之父胡秉宸和肉身之父顾秋水的塑造,构筑了关于父亲的“全部历史”;苏童在《河岸》中借父亲库文轩的潮起潮落,隐喻权力对人的改变和扭曲;郑执通过《仙症》写出“子一代的离散”和对成为父亲的恐惧。向迅一面以《与父亲书》写不加美化与修饰的真实的父亲,一面在《小镇艺术家》《我所认识的巨翅老人》《父亲失踪史》《沙之书与巴比伦花园》《白色灯塔》中写失意落寞却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两种文体交错缠绕、互为镜像,写出的是父亲的复杂和简单、脆弱和强大以及幻想和务实。这是属于向迅的父亲记忆和文学想象,也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物形象和璀璨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22&ZD2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杨,文学博士,《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