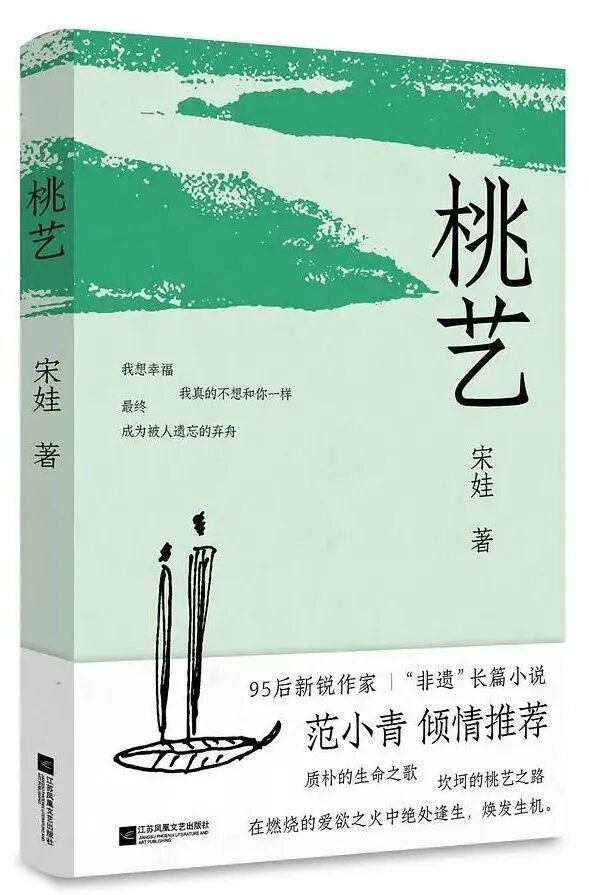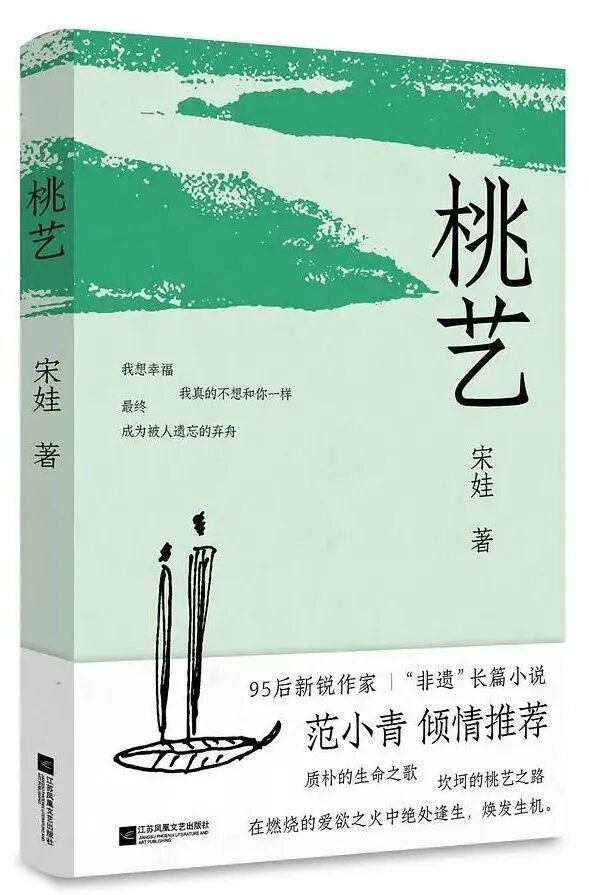
《桃艺》是宋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她在起步阶段就勇敢地扫除了这一文体上的巨大障碍,为自己未来的写作开创了无限可能。对宋娃来说,这一定是自己写作道路上的一个尖峰时刻,以至于这一时刻注定会成为她以后写作之路上一座象征性的灯塔。这是一个值得被反复记取的时刻。尽管此时此刻,关于自己未来的小说之路,一切都悬而未决。
写作《桃艺》的宋娃,一定有她的小说抱负,也一定有她的困惑和迷惘。《桃艺》的完成,是对于暗夜想象的暂时告别,也是另一些深思熟虑的故事的再度重启。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关于宋娃写作的清晰图景,但也可能要适时地承认,宋娃这一代青年写作者必将会为我们提供关于长篇写作的新的行动和力量。他们在冗长的黑夜中,踽踽独行,奋力挣扎,却同样享受着智力上的自由和愉悦,我还无法也无意为他们的写作定性,而更愿为他们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意志表达一点应有的赞赏。
在《桃艺》中,宋娃思考了很多问题,比如传统、现实、爱情、伦理、欲望、人性等等,这都是长篇小说复杂体系中的应有之义。小说的起点是“桃艺”,但落脚点是和“桃艺”有关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娃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关注到了小说的核心和要点——那就是对人的发现和探索。当宋娃将自身的目光投射到她所建构的小说世界时,人首先成为了故事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了故事的承载者。当然,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一个青年写作者在长篇写作上的初步试探,既有小心翼翼,也有无所畏惧,既有孤独的回旋,也有激情的坚定,既有对象征的迷恋,和对隐喻的执着,有在传统之中追溯意义的胆识,更有对隐藏在现代外衣下的人的复杂性的痛击。这是一个偏于通俗的故事,但却俨然一副严肃的、不容轻蔑的面孔,它是偏于情感的浪漫表达,但也不忽视对小说美感的追求。由此,才有了《桃艺》以及和《桃艺》有关的一切。
1
事实上,在读宋娃的长篇小说《桃艺》之前,对于这一“非遗”文化我并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什么实质性认识。我唯一能记起的,是初中时学过的一篇课文《核舟记》。作为一篇说明文,《核舟记》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技术的精湛、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桃艺》要给我们展现的,则不仅仅是“桃艺”的成就和技艺,而是和“桃艺”发生着密切关系的一个个具体的人。
“桃艺”是一门传统技艺。宋娃对于“桃艺”的书写,体现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赞赏。她竭力从传统的技艺中去捕捉一些被现代人遗忘的品格和精神。这在当下的青年写作者中并不多见。但实际上,“桃艺”在小说中不仅仅是技艺,而被凝练为一种精神。这其中就包括爱情——张根对李桃香的爱,“她不是她,她是桃艺,桃艺就是她”。在这个意义上,“桃艺”具有了一种深重的象征意味。此时,张根对“桃艺”的爱,和他对李桃香的爱,水乳交融般地化为一身,那种作为个体的感性和加之于技艺上的才华,推动着技艺和爱情不断地超越其本身,而获得了一种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
但如果我们更深一层来思考,其实张根也是“桃艺”,或者说张根才是“桃艺”。“桃艺”成为“非遗”的艰难之路,和张根这个人物的成长之路是相辅相成的,甚至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复调”模式。“个体化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他或她通往事实上的个性的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些障碍。事实上的个性并不容易实现,而维持起来则更加困难。通常用来象征身份的事物如走马灯一般更替,而其受到推荐的选择又有一种特有的不稳定性,因此,追求个性就意味着毕生奋斗。”其实,张根最后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对自身个性的坚持,以及他对“桃艺”这门技艺的维护,这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事物。由此,“桃艺”具有了更为多重的象征意蕴,并增强了这部小说的丰富性。 当然,具体到小说文本来说,同样具有象征意味的,还有桃源村。在小说中,这既是一个现实的乡村,但也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创造的这个极具象征性的理想之地,此刻被宋娃进行了借用。当然,这样的借用其实并不新鲜,但毫无疑问,这是宋娃笔下的“理想国”。当然,对理想的期许并不影响宋娃对现实的观察和判断,她也不会无视现实中那些最为芜杂的存在——人性之“恶”(勾心斗角、仇恨、嫉妒、报复等等)。因此,桃源村之外对应的那个世界,是美好事物之外的另一方天地,它岌岌可危,危机四伏,却又是人生必须要面对的应然之所。 小说中的桃源村和十里河村隔着一条河,李桃香往来其中依靠的是一条渡船。因此,船无形中也成了小说中的重要象征。“李桃香没有注意老船公对她说什么话,因为她正紧紧盯着眼前老船公这船体上那处疤痕发呆。她认为这船身形态跟自己现在挺着大肚子很相似,不仅是外观,心中感受也接近,每时每刻都承载着许多压力,在来自外力一根竹篙的掌控下,完全由不得自己。只到老化殆尽时,最终成为被人们遗忘的弃舟。”实际上,这条渡船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而每一次出现似乎都预示了一种独特的含义,它是搭载着李桃香驶向外面自由世界的一条船,也是承载着她简朴、纯真的情感的一条船,因此,这是一条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人生之船。渡己渡人,都意义非凡。 除了象征,还有隐喻。宋娃擅于使用隐喻,她用隐喻重新塑造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这种隐喻一方面是通过人物的“身份”表现出来的,小说中,李桃香的身份是多重的,陈伯水的身份也是多重的,这种多重性本身就构成了矛盾,“‘身份’之观念无论何时出现,都被一种内在的矛盾所撕裂:它暗示了一种区分,但是在身份的伸张过程中,此区分往往又被抑制——同时,它指向一种统一性,但是该统一性只有通过分享差异才能够建构起来……”而另一方面,是通过陈伯水的残疾体现出来的。残疾也是一种隐喻。作为残疾人的陈伯水,和作为健康人的李桃香,全然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共同生活时的世界,一个是李桃香离开他时所寻找到的新世界。而这一区分的造成,源于双腿的“行动力”。“通过行动,人走出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世界,在这一重复性世界中,人人相似;通过行动,人与他人区分开来,成为个体。”可以说,正是通过行动,李桃香成为了桃艺,成为了她自己,而不能行动的陈伯水,则恰恰不断地在迷失,“人想通过行动展示自身的形象,可这一形象并不与他相似。行动的这一悖论性特性,是小说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假如说自我在行动中无法把握,那么在哪里,又以何种方式,可以把握它?于是下面的一刻就到来了: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抵达自己的陈伯水,同样的,只能选择回到内心,就像小说最后那个看似圆满却令人无比伤感的结尾: 陈伯水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日子虽然过得无忧,但每天他还是改不了将轮椅滑到大门前对着白果树下眺望的习惯。他常跟保姆说,只要自己对着白果树眺望,李桃香就会回来。 在后面的相关论述中,我可能会不止一次地提及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它当然不仅仅是一次叙事的简单完结,在这个结尾中,其实涵盖了更多复杂性的内容。它有着一种鲜明的隐喻特征,它和过去依然建立着十分清晰的真实又残酷的联系。陈伯水看似是回家了,但实际上,他真正的情感流亡才刚刚开始。只要李桃香不回来,这种理想化就会一直持续,一个回溯中的过去将成为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阴影和桎梏。
2
因了“桃艺”这一象征性的传统文化符码,作为小说文本的《桃艺》自然地具有了一种浓郁的传统性。但我们也不要被这传统的表象所蒙蔽了,实际上,在宋娃坚硬而扎实的现实主义书写之下,她依然抱持着对某种现代性神话的迷恋,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小心地抵抗着那些传统的诱惑,从而用一种更复杂的眼光来审视《桃艺》的叙事魅力。 《桃艺》是向传统的致敬,它写的是“桃艺”这一传统文化技艺在当下时代的传承和发展。这本身就有一种历史的厚重。那承载着时光幽灵的技艺,在当代时间的氤氲中重新焕发出自身的活力和生机。即便是在现实的时间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桃艺”作为一门技艺的文化力量。它塑造着人,也改变着人。 《桃艺》的写作手法是传统的。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宋娃并没有选择当下时髦的叙事模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最为朴实的“现实主义”之路。正如范小青在《桃艺·序言》中所言:“1995年出生的年轻的宋娃,走了一条扎实的现实主义的路,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桃艺》,写作手法上没有玩什么技巧,也不见有什么先锋的色彩,却是着力地塑造了人物,着力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犹豫、多变,和最终的向善等。”确实是的,在《桃艺》中,宋娃并没有过多地用特意的语词手段和修辞手法来呈现叙述的繁复,也没有采用先锋的技法和宏阔的诗情来构建叙事的高塔。她只是借助于“桃艺”这一简单的事物,来讲述故事,来创建新的文化记忆。简单却不失魅力。宋娃在《桃艺》中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建构性叙述,这是一个包括了诸多典范性个体的故事——关于“桃艺”和爱情,以及它们的现实、未来和可能。宋娃写作《桃艺》,是对过去时光的雕刻和纪念,并使之对现在的生活有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以“桃艺”为代表的静止的传统文化,无意中和流动的现代文化形成了对照。“流动的现代文化,不再觉得自身是一种诸如历史学家与人种学家所记载的学习与积累的文化。相反,它似乎是一种脱离、断裂与遗忘的文化。”这就是当下无可回避的文化困境,尽管我们努力在靠近传统,但实际上离传统却越来越远。传统文化所留下的精神诺言,早已经在当代人疲惫的躯体中销声匿迹。虽然宋娃在《桃艺》中没有直接展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但很显然的,她也在无意中越过了那简单的文化狭隘主义的目光,而注意到了技术时代各种先进机器对于传统技艺的冲击和侵害。机械复制时代的“桃艺”,由此也具有了一种不可被取代的人性温度。 《桃艺》的故事和写法是传统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本身具有现代意味。“《桃艺》不同于通常所读到的年轻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它是朴素而郑重的,是舒缓而激烈的。一个传统的故事,一种传统的写法,却有着浓烈的现代感、时代感;两男两女爱恨情仇的情感纠缠,在通俗故事的外表之下,呈现出的却是生命的倔强和无奈;在传统简朴的叙述背后,是人生的惊心动魄,是人性的多重考验,是行业的跌宕起伏,是社会的繁复背景和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因此,除了传统的一面,《桃艺》还有现代的一面。这种现代主要体现在宋娃对人作为一个个体的那种两难困境的发现和探索。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这种两难困境的挣扎。张根和李桃香、张根和吴琼、张根和陈伯水,李桃香和陈伯水、李桃香和吴琼等等,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事实上,关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很难用一种简单的价值观念去判断。“相对于现代进步主义‘不断改进’的观点,回归日常生活的道德恒定性源头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它的意义并非构建一种对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拒绝’,而是一个超越由内部指涉体系所主导的世界的初步尝试。”张根在李桃香和吴琼之间的情感纠葛,李桃香在张根和陈伯水之间的道德犹疑,张根和陈伯水之间的命运牵绊,每一种都令人唏嘘和感叹。但《桃艺》依然试图在这个价值混杂的时代,寻找一种能够激励人前行的道德力量。这也是宋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向善”之心。 小说中,张根和李桃香这两个人物是最核心的。但是最让人同情的,却是陈伯水。曾经健康的他,因为一次矿难而失去了双腿。由此,他和李桃香之间的感情也从一种健康状态陷入了一种病态。失去了双腿的陈伯水,也失去了自由,更失去了情感上的安全。“虽然要是没有自由与安全两者的结合,有尊严的或者令人满意的人生就不可设想,但是,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完美平衡却很少能够达到:如果说过去那些数不清的而且总是免不了失败的努力可以多少作为证据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平衡或许可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陈伯水的一生注定是悲剧性的,那些在小说中作者努力做的精神安抚,实际上都是无效的,这从小说结尾就可以看出来。 小说中,张根、李桃香可以重新发现自我,甚至连曾经的“坏人”吴琼、大王都可以重新发现自我,但身体残疾的陈伯水,无论如何都无法重新抵达自我。这就是他在小说中的宿命。一心向善的宋娃,对于陈伯水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但也正是这一点显示了宋娃作为一个作家的适度,作家不是无所不能的,哪怕是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命运,他们都要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那些致命的时刻一旦出现,它就必须接受那必然的后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可被理解为具有那些会带来后果(即后果性)的活动之宽泛特质,而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这种活动。但就每个个体来看,其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都是非后果性的,而且也不被认为对人们的整体奋斗目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然而,某些活动(如工作范围内的一些活动)却通常被人认为比其他活动更具普遍的后果性。”对于陈伯水来说,失去双腿的那一时刻,一切结果也都已注定。
一部小说,不管依托于何种事物,其落脚点还是在人,在人的情感。那些承载在人物身上的情感,多多少少都转化为我们自身的某种心灵投射,而这也是小说的意义所在。阅读《桃艺》,你可以对这门技艺着迷,也可为现时代中人的困境唏嘘,但其最触动人心的还是小说中的情感部分,以及由情感所带出的道德美感。 《桃艺》的另一条叙事脉络所呈现的,是个人在情感上的逐渐成长。张根、李桃香、陈伯水、吴琼,都经历了这种成长的阵痛。宋娃似乎是通过这种情感上的成长,以及成长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告诉我们,当下人的情感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现如今所谓之‘个人的种种关系’这一术语范围为私密关系和自我表达提供了机遇,而这些机遇在许多较为传统的语境下显得很是缺乏。同时,在某种特定意义下,上述关系则会变得既有风险性又有危险性。与性生活及婚姻生活相关联的行为及情感模式已显得愈来愈多变、不稳固和‘开放’。”张根和李桃香、吴琼之间的情感,就是这种多变、开放和不稳固的最好的明证。 和当下大多数小说中情感的晦暗相比,宋娃在《桃艺》中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透着明亮色彩的情感。而这种基调,似乎从小说一开始便建立起来了。虽然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错综复杂,但大多时候他们呈现出的是一种健康的精神样态,哪怕是嫉妒、诋毁,也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宋娃还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她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依然保持着最大的爱。“在浪漫派看来,培养感受和欲望本质上意味着一件事:唤醒、培养并改善爱的力量。”因此,《桃艺》的最终目的,是借助张根对“桃艺”的爱,展示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最为缺乏的。“浪漫派相信,这在本质上是自我实现,是对我们人性和个性的发展,因为爱是我们人性的核心,我们个性的中心。”因此,如果要问《桃艺》中这些人物最大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他们都是有爱的,正因为有爱,他们才最终完成了自身情感上的成长,并成为了他们自己。 当下时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盛行,而浪漫主义似乎并不为写作者所倾心。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如果连浪漫主义的基因都抛弃了,那其“青年性”想必是要大打折扣的。“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活着就是要有所为,而有所为就是表达自己的天性。表达人的天性就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可表达的,但必须尝试着去表达。这就是苦恼,这就是难题。这是无止境的向往。这是一种渴望。”《桃艺》是否满足了宋娃浪漫主义的想象,我其实并不笃定,但我看到了她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和追求。 《桃艺》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身处现实世界,但身上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张根对“桃艺”的执着,李桃香对爱情的追寻,陈伯水对李桃香的痴情等等,都十分清晰地将这种色彩描绘了出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实现了自身的自由。“既然我们必须自由,必须尽最大可能成为自己,伟大的美德——一切之中最重要——就在于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本真(authenticity),和浪漫主义者所说的真诚(sincerity)。”也因为这种本真和真诚,我们才能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感所打动。 因此,《桃艺》还是一部浪漫主义之作。这从小说的结尾同样能够看出来,回到十里河村的陈伯水,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那份爱,但他同时达成了与残酷现实的部分和解。他也从冲动回到了理性。“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所发现的存在的所有方面,它都是作为美去发现的。”“桃艺”是美的,作为“桃艺”一般存在的爱也是美的,在“桃艺”映照下的人也因此都变得美了起来,这也是宋娃自己对当下世界的理解——世界是美的。“美是当人不再有希望的时候最后可能得到的胜利。艺术中的美就是从未被人说过的东西突然闪耀出的光芒。这一照亮伟大小说的光芒,时间是无法使它黯淡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总是被人遗忘,小说家的发现,不管多么古老,永远也不会停止使我们感到震撼。”那些我们不能在现实中发现的美,宋娃借助小说《桃艺》发现了,这一方面促成了文本对于现实的抗争,另一方面也由此来提醒我们,生活中不是没有美,是我们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和心灵。 《桃艺》试图从传统中寻觅古老的诗情,来给现代人的失魂落魄以心灵的安抚,但事实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地陷入生活的困境之中,加之自身的各种局限使得自我的发展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但毫无疑问的,通过恣肆的想象,通过记忆的重组,以及各种经验的发掘和再造,宋娃极大地改变了她所建构的小说世界的实际内涵。通过《桃艺》,宋娃完成了和时间的对话。“‘与时间展开对话’恰是自我实现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任何给定时刻,它都是使生命趋于圆满的必要条件。”《桃艺》的写作,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体的怀旧范式,只要我们试图和真实的生活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对过去的想象就不会停止,尤其是在这个缺乏道德统一感的时代,直接的情感表达其实已经变得越发艰难,而小说也因此成为我们传递真实感受、增加道德厚度、重建内在生活的一种必需。
韩松刚 :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为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著有《词的黑暗》《谎言的默许》《现实的表情》《当代江南小说论》,曾获第十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