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5周年,在相关的纪念活动中,著名评论家王干,提出“汪学时代已经到来”的论断,引起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2025年5月18日下午,“汪学公开课”第一讲在高邮市汪曾祺纪念馆开讲,首讲人为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孙郁教授。他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三十余部,他的讲课内容为《汪曾祺与新京派文学的形成》。记者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稿件,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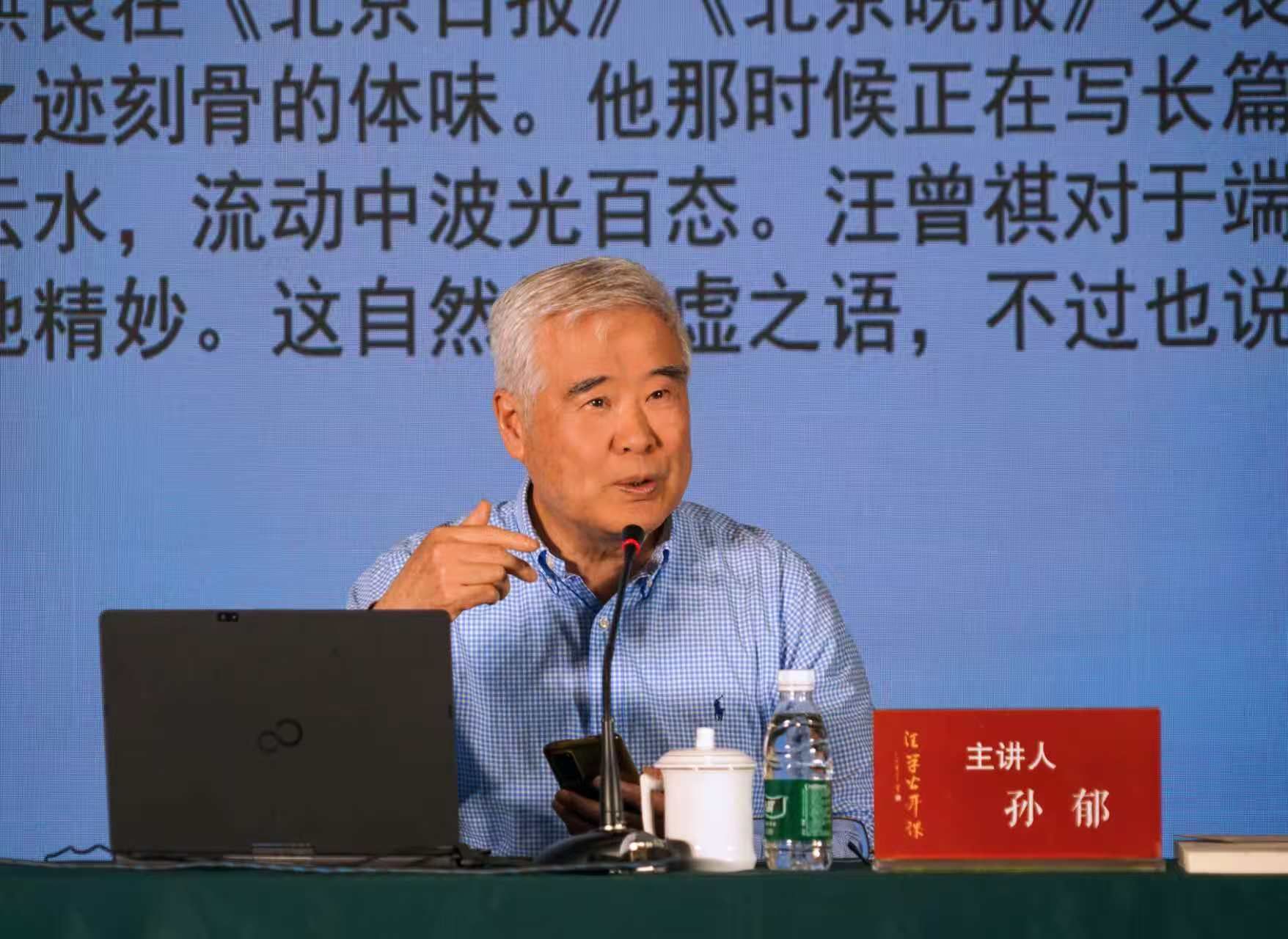
新京派呼应了新康德主义思潮
京派的特点是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的统一,这种资源迎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思潮。实际上,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纠正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思想,将主体性问题引入思想界。而在审美方面,重新发现废名、沈从文,契合了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学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在民俗与语言方面对于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补充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的表述,整合了五四以来人文主义的精神元素,其审美判断与朱光潜、沈从文、林徽因都有相近之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出现是历史链条的一次衔接,或者说,左翼精神与新京派思想,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交叉的部分成了的审美的生长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张中行、徐梵澄、舒芜、陈平原、止庵等。文学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张中行《顺生论》一书关于生命哲学的认识,许多从“苦雨斋”主人那里来,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续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学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学科界限,显得比“苦雨斋”群落更有气象。
汪曾祺与同时代人
在汪曾祺所处的时代,还有一些和他同行的人。
端木蕻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端木蕻良成绩引人注意。汪曾祺对于端木蕻良是颇为欣赏的,以为自己的文字不及他精妙。这自然是谦虚之语,不过也说明端木蕻良在那时候北京作家心目中的位置。但是在新京派作家中,端木蕻良的影响一直不及汪曾祺。端木蕻良不是回到日常,而是走入神秘和高不可及的山路。而汪曾祺则还在人间烟火里,于市井与野地中,生出苏轼式的仙气,与读者的距离近。汪曾祺散文的神韵,是受到端木先生影响的,比如回忆人物的文章,善于从细节出发,在平淡处露出学识。汪曾祺颇为喜欢。我们看他谈沈从文、金岳霖,也用了类似叙述方式。但端木先生的文章,还保留着时风里的某些概念,而汪曾祺没有,完全是一清如水,显得更为纯粹了。所以,端木蕻良是身后寂寞,汪曾祺则火遍全国。
还有宗璞,曾经也受过左翼影响的宗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写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篱,父辈的西南联大的经验和己身所历所感,使她衔接了更为多元的思想传统。其小说多了旧式京派没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而精神趣味则留有废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迹。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延续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遗绪,但感时忧国的一面也历历可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野葫芦引》写得百曲回环,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气缭绕其间,而忧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识人的一种情怀。
还有张中行,晚年的张中行一直为普及老北大的学术思想默默笔耕。他在总结五四以来的传统时,对于鲁迅精神与胡适传统同等对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学理支撑。张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他以为民国作家中,“苦雨斋”群落是不该忽视的传统。《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运,让人想起古代笔记,有人从中读出《世说新语》的味道,也是有道理的。张中行的知识谱系,不是俄苏的,哲学上喜欢康德和罗素,诗文则在六朝与宋明之间,对于自己的老师周作人的古希腊研究与民俗研究亦存心得。北大的传统对于他来说,一是在知识论层面可以究天人之际,而在审美论方面则遵循个性,凝视内心的深处。
较之于张中行的怀旧心绪,汪曾祺对于“苦雨斋”资源的借用显得意味深长。一是文章观念的沿袭,对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观念有诸多心得。一再提倡文白相间的新文体,恰是废名、俞平伯等人坚持的观念;二是对民俗学的看重,小说与散文间的方言、习俗、信仰的描述,呈现了丰富的人间图景。这似乎也呼应当年歌谣调查的遗绪;三是对于儿童学的看重,在风俗里体现童心之美。游戏里的无意义的意义,乃是中国士大夫文学里稀缺的元素,这些对于功利主义文学都是一种消解;四是重新认可非正宗的儒家的价值,从更高的层面肯定原始儒学的朗健、平和之风。在复杂的文化之中,不再选择偏激主义的思潮,而是以中和之音,表述内心的宁静之美。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国时期京派的传统得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剂良药。新京派作家的写作深化了对于“苦雨斋”传统的认识,而且那些沉睡的灵思在今人的现实忧患里被重新召唤出来。
张中行虽然在九十年代颇为红火,身后也没有汪曾祺那么有名气。这可能是他的界限过于分明,坚守“苦雨斋”的传统,思想上沿袭罗素、康德精神。对于激进文化持批评的态度。
汪曾祺与张中行比,学识略逊,而并不在观念上划线,对于各种流派,咸能视之,取其佳者而用之。前者钟情于朴素的儒学,后者则注重西方哲学与佛学,有《顺生论》《佛教与文学》行世。
汪曾祺为何能够成为新京派的代表人物?
首先是汪曾祺脱离了旧京派的象牙塔气。汪曾祺与南星不同,南星欣赏白洛克、露加思、劳伦斯,大概是审美方面的不合时宜。他们置身于现代社会,其表达却是现代社会的异端。南星的作品没有泥土与市井气,这限制了他的审美的宽度和深度。汪曾祺在旧式风景里,揉进了广大的民生之色。他的古老的街市里的风景,是活的。
此外,汪曾祺将精英的变为民间的。看周作人写“吃茶”的文字:“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用的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刚从沙漠里走出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了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
汪曾祺写“吃茶”:“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 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谱》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
两相比较,汪曾祺的文字就很通俗,很民间烟火气息。
汪曾祺的写作具有先锋气,主要是看到了对于生活荒诞感的描述。比如《八千岁》中的个人信条在生活中的尴尬,“概不做保”“僧道无缘”的理念的破碎;还有《关老爷》儿子不幸的根源,是父辈生活积习的结果,关老爷的平常里的荒淫,乃社会悲剧的基础。
汪曾祺还具有儒家式的个人主义,汪曾祺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中写道:“有一个评论家说我写的一些人物的恬淡自然的生活态度有老庄痕迹,并推断我本人也是欣赏老庄的。我年轻时确是读过《庄子》。但我自己反省了一下,我还是较多地接受了儒家的影响。我觉得孔子是个很近人情的思想家,并且是一个诗人。我很欣赏曾点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超脱的,美的,诗意的生活态度。我欣赏宋儒的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五四新文学中,儒家与个人主义是对立的。但汪曾祺却在二者间找到平衡。
汪曾祺的文字提供了现象学的标本,以描述取代解释。汪曾祺曾经在《卖蚯蚓的人》中写过:“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
高明的小说家或叙事者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扎根在他的智识无法穷尽的现实领域,刺穿一个个自欺欺人之观念的钟形罩,以按其内在节律、自行其是的语言,唤醒或识别自己身上所拖带的世界,产生一种全景式的恢宏视野和如临其境的现场感。具备了随时转化、调整已知的一切的能力。现代小说家体验他所体验的一切,以其完整的、抵达某种极限的想象力,将零星、偶然、杂乱的日常生活编织或整理成有序的“一次经验”,让叙事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进行,赋予人物强有力的生命,从庸常生活之流中萃取那永恒不朽之物,或指向一些值得敬畏的、比自己更高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