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应用最新版本的下载讯 2025年10月31日,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周荣池散文创作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吴义勤视频讲话。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鲁敏,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薛印胜,扬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勇,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国祥,及省内外1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鲁敏主持。

本次研讨是今年江苏省作协策划的系列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之一。周荣池是江苏青年作家的优秀代表,他出生高邮,著有散文集《父恩》《灯火无边》《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村庄对我守口如瓶》,长篇小说《单厍》《李光荣下乡记》等十多部。曾获茅盾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长江文艺》双年奖。

吴义勤表示,周荣池是文学苏军新生代作家中重要一员,其散文创作展现出深厚的乡土根脉与独特的文化自觉。他善于捕捉里下河地区风物人情中那些细微而深刻的记忆,将水乡的日常劳作、民俗记忆与个体命运交织成篇。他的文字质朴而富有张力,叙事中蕴藏着对故土变迁的浓烈情感,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质与普遍意义的书写风格,为江苏散文开启了新的美学维度。
郑焱在致辞中说,在周荣池的创作中,能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乡土记忆到时代思考”的创作脉络。他始终坚守乡土文化根脉,直面城乡变迁的时代命题,不回避发展中的矛盾与困惑,通过对乡土与城市关系的深度思考,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文学视角,他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资源,以细腻诗意的笔触、沉稳厚重的文风,构建起一个充满“江苏记忆”与“人文温度”的散文世界。
周荣池的两部近作《父恩》和《灯火无边》均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薛印胜表示,周荣池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扎根里下河平原,以宽广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城乡变迁中中国面貌,浸润着对乡土中国的深情与思考。
江勇和赵国祥介绍了当地文学的发展情况。江勇说,周荣池是扬州的代表作家,多年来,他扎根基层、潜心创作,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完成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赵国祥表示,周荣池持续书写家乡的沧桑变迁与人民的情感世界,其作品既有对乡土生活的精准捕捉,又兼具雅致的文学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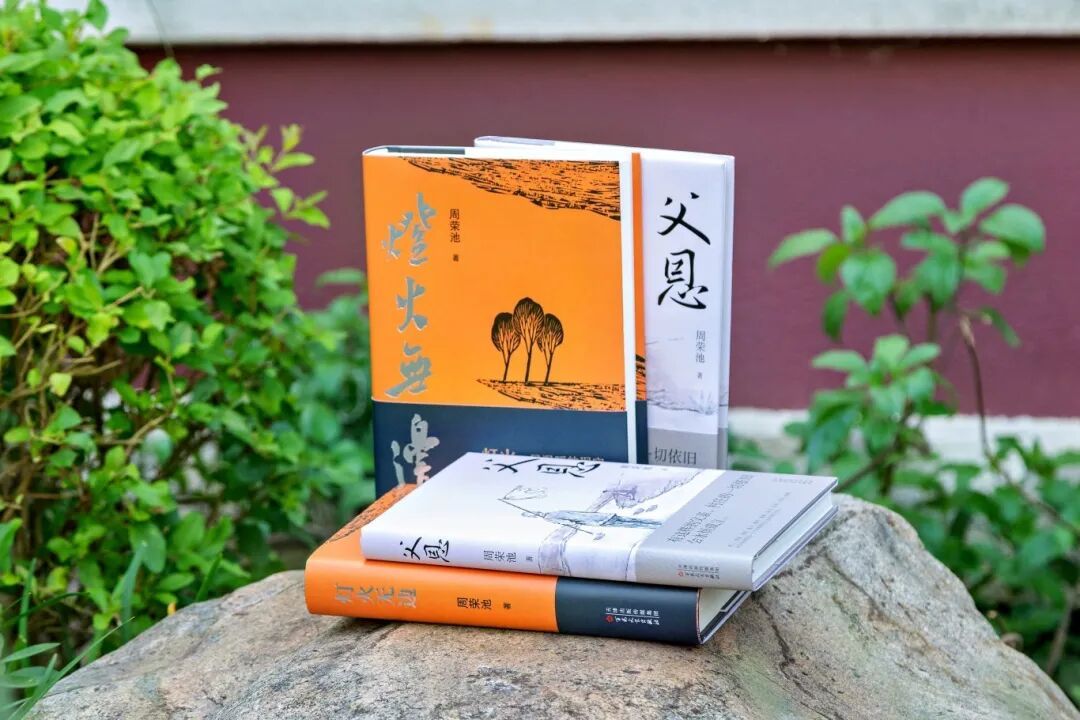
乡土世界:
以南角墩为中心向外辐射
“这是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一部关于里下河乡村的沉思录,也是一首里下河乡村的抒情诗。”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徐可概括阅读《灯火无边》的整体感受时说。
“里下河南角墩”是周荣池文学世界的中心。“他的整个创作聚焦这块土地”,《散文海外版》执行主编王燕说,《父恩》也好,《灯火无边》也好,他写了很多身边的人,他没有跨出这个圈子,所以不仅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卑贱与高贵,也写出了他们的永恒与不朽。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即便在当下,依然有诸多创作者持续耕耘,也由此带来大量同质化作品。2020年,在周荣池《一个人的平原》研讨会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直指要提防“乡村博物馆式写作”,仿佛乡村在时代当中凝固了。“过了五年,周荣池的变化很大”,反观其近期创作,以《父恩》为例,他用一本书的体量去写父亲,父亲出生于1949年,正好是一个人的共和国史,“父亲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正好是中国乡村剧变的整个过程”。这本书不仅是对父亲的审视,也是周荣池自己作为人之子的精神世界的打开。
“《父恩》是有根的,它植根于乡土,写父子的关系,也是写自我与乡土的关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饶翔说,周荣池的乡村书写直面大地,直面大地上的生存,这种生存既是贫困的、卑贱的、野蛮的,又是倔强的、坚韧的、自尊的、有情有义的。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亦将《父恩》视作周荣池新的散文写作的开端。“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试图建立一种以乡土经验为底色的现代生存哲学,”韩松刚说,一方面,他从早期对乡村器物、风物、日常生活的物质的、自然的书写中摆脱出来,在《父恩》和《灯火无边》里,农具或作物已不再是日常装饰性的东西,而是拥有自身存在尊严的主体,作品呈现出一种本体论式的城乡意象;另一方面,《父恩》和《灯火无边》出现了带有一种抵抗性的转向,他不是要逃离乡村,而是通过构建一个他所理解的经典的乡土世界,来映照现代社会的残缺和不足,给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补给。
周荣池的写作依然立足南角墩,又沿着这片土地不断向外辐射、向内开掘。“《一个人的平原》《父恩》《灯火无边》在我看来是他的三部曲,”省作协副主席汪政说,类似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一个人的平原》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整体性写作,到了《父恩》集中到一个父亲的形象上,然后由这样一个个别形象再次进入普遍,就是《灯火无边》,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进入了新的高度。
中间位置:
解剖城乡变迁中的两栖心态
这些变化映照的是周荣池近几年对城乡关系的思考和体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注意到,周荣池反复提到农村哺育了城市,不同于通常从工农业剪刀差来谈农村反哺城市的问题,周荣池是从感性、从人和大地关系的本真现象上去讨论这个问题,而这一观点也依赖于他对城乡区别的洞见。“他说城市和乡村的供养方式不一样,在乡村只要有一块地,你就有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于是有自给自足的自信,而城市人是消费性的,是无法自给自足的”。他写出了一种复杂的城乡心态,这种城乡两栖心态也对应着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它本就处于一种停滞和茫然的两栖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周荣池不仅写出了城市和乡村,也写出了一个更深刻的时代。”
“他不仅是农村出身,还长时间是一个基层治理者,他跟地方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坚实的甚至是执拗的联系,创造了他的文学世界。”《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说,他引用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这个概念,来读解周荣池的写作,“他一定要通过感知周边,建构坚实的具体经验,来形成自己的主体。”如同米沃什描述过的“小地方人的谨慎”,周荣池的主体意识里,这种小地方人的谨慎和执拗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其文学品格和个性能够形成的重要依据。
特殊的经历赋予周荣池特殊的目光和位置。何平提出,周荣池的写作提供了一种“中层知识分子看乡村”的书写位置,这个中层不是社会阶层的中层,而是指空间上不属于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而是处在小城镇上的知识人看乡村的位置。“这种中间位置提供了一个观察乡村、观察城镇、观察中国社会的很重要的角度。”
“作家写作品要有距离,距离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栾梅健同样用“中间”来描述周荣池所处的写作位置。他说的“中间”是作家相对于笔下人物的位置,太高了像俯视,太低了缺乏理性反思。在栾梅健看来,周荣池的散文是对现代文明的冷静思考和对乡村生活饱含感情的描摹,是介于理性与情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创作。
说起位置和距离,《当代》主编徐晨亮提示,周荣池的近期作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是“无边”,不管是《灯火无边》,还是新作《无边的城乡》,他关注的问题是没有边界的。“他的作品里充分贯穿了城市和乡村双重的眼光。”《父恩》重新定义了恩是什么,“并不是父亲对我的爱构成了恩,不是父亲给我的精神财富构成了恩,而是他跟他的周边环境矛盾冲突给我的强烈启示,是‘父恩’,这样定义父子关系,非常具有突破性。”
徐晨亮将之与詹姆斯·鲍德温的《回归故里》对照,认为周荣池的写作也是一个回归故里式的写作,和当下的精神处境有密切联系。“和很多年轻作家不同,他的世界性不是仰赖于模仿和阅读,而是在个人经验长时期的熬煮中获得的”。
汪政将这种切身切骨的经验概括为一种“地方感”,他特别强调“感”的重要性,“感”要求身体要在场,周荣池写《父恩》,他的身体跟父亲是相通的,是有身体感受的。“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要这样写出活的自己,写出活人感。”
细节之锚:
在真实肌理上还原生活图景
“《灯火无边》不是一些散文文章的合集,而是一个有结构、讲体例的整体的长篇散文创作。”在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西安市作协主席穆涛看来,这里面,上中下三篇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划分,而是有着整体的思考。作品以城乡之间的精神纠葛为线索,以有意味的细节推动叙事,整个流域的民俗、民心、民愿,记录得真实生动,构成了一种灯火万家的无边的惆怅。
这些鲜活的细节既依托于周荣池的观察和体验,也仰赖于他精准而简洁的语言描述。“他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着具体真切的细节。”省作协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认为,周荣池始终对语言的平庸化有一种警惕,他对风俗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写了很多苏北平原特定区域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的生命态度、生活方式,但这些始终是和对特定人物的塑造、对特定人物心境的刻画融合在一起的。
“散文除了描写,还有叙述,”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分析指出,“叙”就是讲我从前的故事,“述”不只是在讲这个东西,更要讲述出我对它的判断感受。“周荣池的写作‘述’是大于‘叙’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态度和感受写进去,所以他经常在动名词前加上一个形容词,比如‘粮食’前加一个‘瘦弱的粮食’,比如‘疲惫的塑料布’等,都是‘述’的渴望”。
在长期的散文写作实践中,周荣池摸索出了自己的散文观。“作为一位扬州籍高邮籍的散文家,他天然地活在一个文学传统里。”饶翔从文学脉络的角度补充说,经过这些年的创作,他显然从汪曾祺的影响中走出来了,他的散文的语言和精神质地是坚硬的、粗粝的、尖锐的、有一点艰涩的,这种文字语言,增加了它的文本分量。
“荣池的生活背景、成长环境都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省作协副主席、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在名师带徒项目中担任周荣池的导师,他们一起讨论过《父恩》《灯火无边》的初稿,对于研讨会上提到的乡土创作、城乡结构、文学传统等问题,王尧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写作乡土题材,不能只把乡愁作为情感,而是要把它作为思想方法,反观自身、反观历史、反观当下。他不赞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简单划分,认为城乡是互相定义和阐释的,这在周荣池的新作中也有体现。

“我在写作上是一个‘野蛮生长’的作家”,周荣池在答谢时说,其写作总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成长。他表示,自己在四十岁开始思考“中年变法”,在以后的创作中会“守好自己的角落”,相信有文学的善意和时光的恩情,会见到自己的“灯火无边”。(文/俞丽云,图/王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