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毕业于水利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河海大学教师,后任河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2013年,朱辉投到文学最温暖的组织怀抱:taptap下载的游戏。此时,距离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过去近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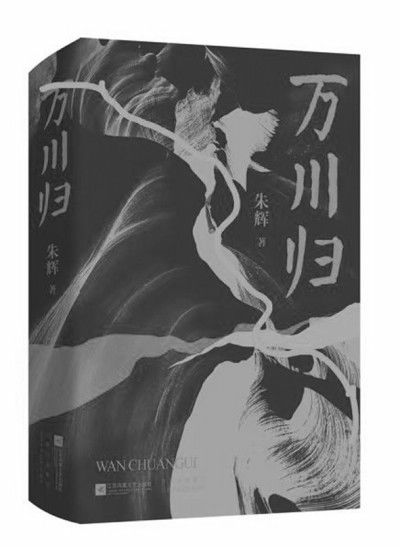
在三十余年的业余创作中,朱辉发表了四部长篇,近百部中短篇。他的目光及笔触所及,很多皆是熟悉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琐事:来自苏北小镇的同乡间的友谊与暗斗(《双风灌耳》),一个小城画家欲说还休的一段情事(《动静》),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和女编辑间的一份暧昧(《对方》),或者,只是校园里的一次意外风波(《狂风大作》《棕色药瓶》),一个退休教授临死前的短暂生活(《红口白牙》)……朱辉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一切,他的叙述贴近对象的琐细与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节中隐含的冲突,他只关心那些与人性、人的隐秘心理相关的细节,尤其留意的,是这些细节背后蕴藏的意义……朱辉的温情掩藏在文字背后,他用温和的理性处理一系列现代性主题。所以朱辉是有亲和力的,他不仅讲故事,我们的境遇、现代人的境遇在他的故事中都能够得到同情和理解。
中华读书报:您的创作线索多来自哪里?《万川归》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朱辉: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的,听来的,看见的,甚至一段音乐,一个笑话,一个梦,都可能是一个作品的缘起。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家,生活直接给他提供素材的机缘,一辈子不会超过个位数。《万川归》是我第五部长篇,此前的《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都是2000年前后写的,像发了神经病,一口气写了四个。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才动念写《万川归》。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事,似乎有无数的话要说。许多人映着二十年的时光,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并逐渐清晰。作家应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眼睛,我看见了他们晃动的身影下,太阳和月亮的阴影,我看到了他们的心,或者说是他们的心跳与我自己的心脏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渐渐有了节奏,有了旋律,也有曲调也有情。我进入了状态。
中华读书报:曾在河海大学学习水利专业的经历,对于小说创作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吧?在把握题材方面,是否游刃有余?
朱辉:水利专业的学习经历,对我所有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万川归》里,归霞和丁恩川就是水利专业出身。对这个行当我有基本的了解,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我还是要请教我的同学,他们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他们才是行家。我曾为没有读中文系而遗憾,但其实除了文学,有一个其他的专业也挺好,它冷不丁或者随时在支持你。如果没有学习水利的经历,《七层宝塔》中有关国土规划的理念我可能就不会有。在小说里也就几句话,但这几句关涉到土地和河流。李敬泽曾在一次会议上蹦出一个词:空转现实主义。那次会议我不在场,是会后别人转述的,我吃了一惊,他总是能语出惊人。对这个词当然有多重诠释,但我想,一个长篇,里面的人物,故事,最好能够落实,倒不是我有写出百科全书式小说的野心,而是人物、情感、思虑和慨叹,必须有所附丽。这个时候,在几个人物中设置一两个水利行业的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这不是一本关于水利行业的小说,书中有好多人物,有教授,有律师,有保姆,涉及的行业除了水利、政法,还有房地产和出版业。我在大学和出版社工作多年,知道不少所谓秘辛,这些都不是问题。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1960年代出生的人30年的生活历程,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分别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还有一个人生活在京杭大运河边上。而这几条大江大河最终都流向大海,“万川归”,小说的寓意大气磅礴。在驾驭这部长篇的结构和表达主题方面,您有怎样的寄托?
朱辉:我在小说开篇就描绘了从飞机上俯瞰的景象,几条大河在国土上流淌,最终归于大海。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还不叫“河海大学”,是“华东水利学院”,其实学生不止来自华东,全国都有。“流域”和“水系”是水利最基本的概念,我把几个人物的出发地安置在几个主要流域,是自然而然的。
百川归海,在中国,大江大河向东流淌,是因为国土西高东低,这是规律,是高程问题、空间问题。时间上,光阴一去不再,人由小变老,也无可违逆。几个人物三十年的成长,必然跟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大潮,在潮涨潮落中发展。中年以后,我对“命运”两个字越来越感兴趣,国家的命运,群体的命运,职业的命运,个人的命运。我希望写出命运感。
中华读书报:小说提到电影《庐山恋》曾风靡全国,女主演张瑜换了四十三套衣服——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吧? 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觉流淌着一种怀旧的情绪,同时也记录了时代变迁中资本的扩张、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您在写作中,觉得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朱辉:《庐山恋》中承载的文化因素很适合我这本书。《庐山恋》1980年开始上映,张瑜确实换了43套衣服。这在刚从“蓝蚂蚁”着装社会走出的中国,是石破天惊的。印象更深的是,女主角居然通过纠正男主角的英语发音而相识,进而通过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清晨)来传情达意。1981年我在上大学,每天爬到清凉山上背单词。电影中的这个场景跟清凉山十分相似,只不过你即便大声说出这句英语,也不见得有姑娘来应和你。怀旧是一种老年病,略微年长的怕是都会有点怀旧,轻重不同而已,这就说到写这个长篇最难处理的问题了——时间。时间跨度三十多年,很漫长,也很丰富繁杂,但并不是什么都能写。我悟出了结构对筛选材料的意义,我捋出了时间线,大事记,为了结构,我想了一年多——摒弃所有杂务,连短篇都只写了一个。突然有一天,脑子亮了。我兴奋地看见了还一字未落的长篇的雏形。长篇的结构有很多种,比我们看到过的各种建筑物还要丰富诡异。我希望能有点新意,最好是别人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非常难,简直是狂妄,我努力了。
中华读书报:您对于笔下的主人公,持有怎样的态度? 万风和、归霞、璟然都是有病的,是身体的病,也是时代的病?
朱辉:没有什么万事如意,疾病或欠缺就是人生。据我所知,人到中年,体检报告上毫无问题的人大抵是很少存在的。几十年的打拼,奋斗,当然也包括消耗性地享受,几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病痛。万风和、归霞、璟然身体都有病,丁恩川、周雨田等人也有暗疾,即便像个天选之子的李弘毅,他身体极其健康,但也遭遇了无妄之灾。但我本意上并不想揪着具体疾病不放,我真正关注的是过程,是趋势,是过程中的悲欣交集和趋势的庄严沉着。
中华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的写作在哪方面变化最大?
朱辉:心态更好了。对文学、对人生的理解更稳定,可能也更深了些,表现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中华读书报:国内的城市题材小说不如农村题材成就大,您怎么看?我认为《万川归》达到了新的高度。不知您本人有怎样的写作目标?
朱辉:中国有漫长的农业农村史,中国的城市还处于发育当中,城市题材的作品也许没有写农村的作品成就大,但这是暂时的,情况很快会发生变化,甚至逆转。不得不承认,农村题材的作品,有时会天然地让人高看一眼,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褒奖,但对写作的人来说,不要考虑这个比较好。写作是性情的事,与做人一样,太精了其实是笨,做你自己就好,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好才是王道。所谓“新高度”,首先应该是我自己的新高度,我的认知是:这部长篇,达到了我目前的最高水平。写的时候,我深知话不可说破,情不可越界,总之我尽力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自己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具有怎样的风格,在同类题材中有何特点?
朱辉:概括的事我做不好,能说出的是:写城市或写乡村,其实都是写人,区别只在于文化传统和生活、生产方式。我特别有兴趣的,是人们习焉不察、熟视无睹的裂隙处。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怎样的期许?
朱辉:我曾经说过,一个小说家,如果能写出五个优异的短篇,或一个优秀的长篇,那他作为一个作家就不枉此生。写每个作品,无论长短,都应该不遗余力。我希望能写得更好。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4月09日 11 版;鲁大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