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江苏作协历来重视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培养,通过组织培训、学历教育、文学评奖、青年论坛等多种方式,帮助青年作家、批评家成长成才。2019年起,先后启动两轮“名师带徒”计划,推出“文学苏军新力量”“江苏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队,进一步建强文学苏军方阵。省作协下属四大期刊同样把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列入办刊重点:《钟山》举办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并联合《扬子江文学评论》举行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设立面向全国青年作家的“《钟山》之星”文学奖;《雨花》坚持做好“绽放”“雨催花发”栏目,承办“雨花写作营”;《扬子江诗刊》设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栏目,每年评选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推出江苏十佳青年诗人,举办长三角新青年诗会等青年诗歌活动;《扬子江文学评论》推介优秀青年学者的批评文章,连续八年组织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学术工作坊……江苏作协多措并举,囊括新鲜“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学力量,展现文学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见证一代青年作家、学者的探索与创造。
近期,江苏文学以全新栏目“文学新火”,与四大点点娱乐场联袂推介具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本期与《雨花》杂志共同推出“雨花写作营”学员、江苏省作协会员——邹江睿。
邹江睿:或许明日太阳西下
作家简介

邹江睿,2001年生,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硕士在读,taptap下载的游戏会员,南京市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青蓝人才,在《十月·青年专号》《青春》《延河》《西部》《青年文学》《四川文学》等发表小说十余万字,有作品被《海外文摘》选载。曾获2020《延河》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头奖、第五届全国打工文学大赛小说组金奖、第八届野草文学奖小说奖、第十三届大学文学奖优异奖等。第六届雨花写作营学员。
创作成果
2020年
《吃土豆的人》发表于《延河》2020年第5期;
《痴线》发表于《青春》2020第6期;
2021年
《蒲公英飘在风中》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青年号》2021年第3期;
《猪脚粉兄弟》发表于《短篇小说》2021年第9期;
2022年
《热气球飞向天空》发表于《青春》2022年第5期;
《富顺棒棒》发表于《青春》2022年第7期;
2023年
《犀牛角镇的南边有什么》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青年号》2023年第3期;
《富顺棒棒》转载于《海外文摘》2023年第5期;
《扁平足与木菠萝枝》发表于《十月》青年专号;
2024年
《倒影》发表于《青年文学》2024年第5期;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发表于《四川文学》2024年第5期;
《太阳照常升起》发表于《西部》2024年第5期;
《北窗》发表于《青春》2024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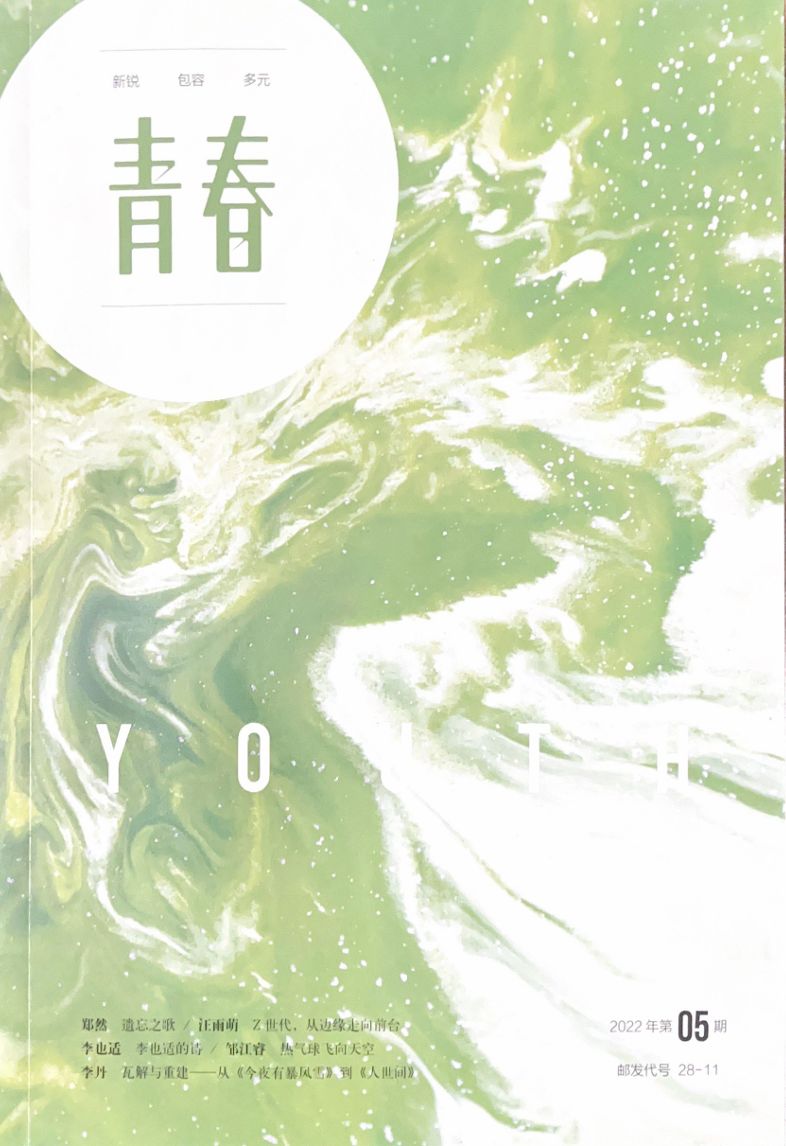
邹江睿部分作品发表刊物
获奖情况
2021年
《吃土豆的人》获2020《延河》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
《吃土豆的人》获第五届全国打工文学大赛小说组金奖;
《杀死那只乖猫》获第八届野草文学奖小说组二等奖;
2025年
《虎将》获第十三届大学文学奖小说组优异奖。
作品选读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节选)
文 | 邹江睿
一
出事那天晚上,一向安静的海子变得异常狂躁。他先是在窗台上来回踱步,神叨叨地,后来就扯开嗓叫个不停。我起床两回,帮它梳毛,按摩,抚摸下巴和胡须。那儿湿湿的,不知从哪儿沾的水,拿来纸巾擦干,过一会儿,莫名其妙又湿了。我气急败坏,找遍家里也没发现水源。末了,仔细一看,罪魁祸首竟是几滴顺着眼角滴下的眼泪,淌在它的脸颊上。
养猫两年多来,这是海子第二次这样流泪。上一回是在刚来我家的那天晚上。它缩在角落里,不吃、不喝,眼泪直流,偶尔叫一声,我才确定它还活着。领养前我半开玩笑地问书生,你说这猫,它会想你不?书生没笑,很严肃,耳朵朝后绷直,眼睛眯成缝,右腿像根朽木拖在身后,跟着他来回踱步。当然会。他说。它们都会的。
那晚从午夜折腾到两点过,海子终于累了,不再叫,僵着身子,靠在窗边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它还睡在那儿,像生了病,只有眼睛隔几秒转一圈。我赶紧给吴妈打电话。她没接,一直占线。过好一会儿,回给我,没等我开口,一句话就脱口而出。
书生走了。她明显哭过,声音肿起来。昨晚走的,人在殡仪馆,你有空来送送他吧。
挂断之前,她又补了一句,叫我把海子也带上。我咳了两声,想说些什么,话到喉间,鱼骨似的卡住,我只能支支吾吾地从声带缝里挤出一声“嗯”,然后匆忙地把电话掐了。
岸边的石头就快坠崖,水即将漫过我的头顶,咽喉里不断翻涌、撕扯的是肮脏的泥水。我把手机往腿上一搁,长吐了一口气。
一团积郁此时落在地上。
二
关于海子为什么叫海子,我问过书生很多回。他一开始忘了,说谁记得这些,后来又改口,说他最喜欢读海子的诗,百看不厌。我获得的最终版本,是他在路边阴暗的垃圾桶后捡到海子那天,不远处的酒馆里正唱着,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这是我最信服的一种解释。吴妈也赞成。她说书生就是这么个人,做什么都没谱,跟猫一样。我说也不一定。有时候没谱比有谱的还来得靠谱,你信不信。
从书生的葬礼回来以后,一向没谱且没心没肺的海子连着三天不吃不喝。
不仅不吃喝,动也很少动,除了必要时去猫砂盆里扒几下,大部分时间都像一堆久积的灰,窝在客厅西南角的立式空调背后。它刚来我家的时候也爱窝在空调背后。一觉醒来,屋子里转一圈,找不到猫,瞥见窗户没关严,有个缝,比划一下,它似乎能很轻松地跃过去,我当即惊出一身冷汗,给书生打电话。我说完了,到我家第一天猫就丢了。书生倒不急,慢悠悠,嘴里还啃吃的,嘎吱嘎吱。不可能。他说。海子宁可躲在马桶盖里喝水也不会跑到外头去。我说你这么肯定,是不是知道它藏哪儿了,他说当然,我当然知道,我闭着眼睛也知道它往哪儿跑,钻到哪儿去,不然我瘸条腿,怎么折腾得了。我说那你倒是快讲呀。他不肯,留下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找猫也是养猫的乐趣之一,就把电话挂了。他说这句话时明显在笑,边笑边咳嗽。我恨不得隔着听筒像掐草穗一样掐他的喉管。
当然他说得没错。从床底下或者空调背后把海子拎出来日后已经是家常便饭。它乐意和我躲迷藏,我乐意找他。人和猫之间的娱乐就这么简单。就像它吃我的粮食我也欣然喂它一样,谁都没多想。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死在家里海子也许会把我吃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好几次我假装踉跄摔倒在地一动不动。为了逼真我甚至大气不出一口。它晃悠悠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憋得面红耳赤。它不急,在我脚趾那儿晃两圈,闻闻,又绕到另一边,再闻再嗅。最后它看到我实在憋不住气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时就失望地走开了。我把这些说给书生听时他笑得前仰后翻合不拢嘴。我恼怒,问他,这有什么好笑的?你怎么知道猫哪天不会变成老虎把你大卸八块?他说这你放心,用不着猫变老虎,我本身就瘸了腿,接下去死掉也不是没可能。他说我要是死掉了最后一句话一定会对它们讲:晚安,我的小猫。说完他朝旁边的地上啐了一口。我对着那口痰也对着他的脸狠狠翻了个白眼。
后来他有没有照做,我不清楚。只是某次无意在书生留下来的一沓书里,读见海明威临死前的遗言也是那句:晚安,我的小猫。吴妈告诉我,书生倒下那晚在他二十平米的小屋里簇拥着十三只老猫和他们的崽子。她说它们并排站在书生旁边,对着头呀,脚呀,身子呀分毫不动就像是一群士兵对着战死的将军立正稍息行默哀礼。庄子、落花生、迷迭、紫藤萝、逵儿……怪名不少,吴妈认得大半,还有些叫不上名。她走过去,给书生身上盖上毯子,有几只瞥了两眼,没动。楼下警笛鸣响,她跑出去,接车、带人。再回来时十三只大猫小猫短短几分钟内蒸发得一只不剩。她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半晌没声,直到医生在背后捅她的脊骨,耳边才听见两声AED的嗡鸣,有人拍着她的肩膀,说,人没了,节哀吧。她说她后来老是幻听那个声音在耳边窃语,人没了,节哀吧,句句清晰。眼前跟着浮现的是猫群集体哀悼的场景。我说你别讲了,怪吓人的。她白我一眼,说,这还吓人?十三只猫像幽灵一样来了又走,我可是亲历者。
于是后来我的疑问就变成了,如果我倒地死去,海子会不会领着子孙后代排成排来祭奠它的主人。这问题显然在海子被我剥夺当爹权利那天就不了了之了。整件事里受害者一位,嫌疑人有三个:书生提议,吴妈操刀,我负责坑蒙拐骗。它被推了麻药端进手术台时我和书生就在宠物医院门口抽烟。他坐在轮椅上,我倚着墙,抽的是红南京,两个人一场手术抽掉一整包。我说你接下去打算怎么办?他反问我,什么怎么办?猫肥家润,卖点书买点粮,还要怎么办?我说你不谈恋爱不结婚不要小孩?你难不成一辈子跟猫过?他说我瘸啊,谁会找一个瘸子。我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不说话了,闷头一个劲抽烟,脖子顶着脑袋左摇右晃,末了伸手,一拍头,说,大不了就这样,有什么不好。我看猫比人靠谱。我说也是,猫至少不骗人,饿了就是真饿渴了就是真渴,说拉屎一定当即就蹲下一分钟都不多待。书生对我的话显然很赞成。他赞成别人的方式就是狠狠拍对方的屁股。他对猫咪表达爱意时也会拍它们的屁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坦诚相见。人和人之间是很难如此坦诚的。他说这话时眼睛直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的身后。我的额头因此一阵一阵地发热,似乎有拳头一下一下捶击我的脑门。
后来再有类似的感觉,是在书生的葬礼上。他躺在殡仪馆守灵厅玉白色的大理石台面上两腿伸得笔直,谁也看不出他的残疾。某些角度甚至让我觉得他像是睡在被窝里那样舒服。吴妈先上前,哭了一阵,说了些话,我都没听清。轮到我靠近时我抱着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书生眼睛闭着,脸上抹了粉涂了唇膏也擦了腮红,一向乱七八糟的头发理得可直、可顺,一尘不染。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像是隔着一面磨砂玻璃那样模糊。他在里头,摩挲玻璃,叩叩指节,声音回响在棺材板间,低语似的,我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听不清但我知道他是在对我说话。我可以猜得出来,想说的无非是别烧纸呀别扫墓呀人死了就随他去,或者是嘲讽下吴妈顺带嘲讽下我,笑我们太矫情,多大人了,还哭鼻子。
反驳的话我最终一句也没说出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忍着,眯着眼,鼻翼一抽一抽,不让眼泪啪嗒落到地上。海子这时开始焦躁不安地蠕动。它显然想往玉石板往灵堂中央往书生笔直的身子上跳。我掐紧它的身子赶紧往回走。
额头就是在这时开始疼痛的。像是左挨一拳右挨一拳,满世界轰鸣,眼前瞧的耳朵听的,全变成模糊的影子,一齐塞进棺材箱里。我后来回忆起这个午后,能记得的只有棺材、疼痛和轰鸣不断,以及那句书生说过海明威说过也许很多人都说过且持续在说的话。
晚安,我的小猫。他趴在我和海子的耳畔轻轻说道。
三
书生说,人可以一辈子不谈恋爱,但有两条绝不可触犯:一不能不养猫,二不能不读书。他逢人便谈书,也送过我几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我丢到柜子里吃灰。他说年轻时他可以一整晚不睡觉坐在沙发上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天亮鸟鸣,读完以后浑身像是浸泡在冷水里,尖锐的冰块棱角刺入他的皮肤,仿佛几千把匕首使他五脏俱裂。他二十多平米的小屋里除了床、衣柜和轮椅以外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一摞一摞的书,每摞书上通常站着几只面无表情的猫和它们的崽子。那小屋也是他的小店,在一条开有早餐铺、修车摊和皮肚面馆的小巷里,几乎是最窄的一间门面。连门头都没有,拿块破木板,写上“收书”,立在门前的梧桐底下。我说你这店铺实在寒酸过头了,换间大点的,敞亮得多,人家也愿意进来。他说那有什么好,打扫起来费事,来的人又多又杂,我个瘸腿,忙不过来。我说你别讲那么多,说到底,不就是缺钱嘛。他愣了下,说,对,你讲的对,说破了就是没钱。
书生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要去一次拉萨,带几只猫,租辆皮卡,去看看那些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他说他们是皮绳扣上的魂而他是轮椅背上的魂。说这话时他黑色镜框背后那双眼睛亮得像太阳。我说什么?什么皮带上的魂?他一时答不上来,想去翻书给我看,又觉得麻烦,干脆不说了,指指自己的胸口。他答不上问题的时候总是这样指着自己的胸口。听吴妈说,心脏骤停倒在地上时书生一只手就捂在胸前。我后来想了很多回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答不上来。我想到很多假设又推翻了很多最后一无所获。这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到死也想不明白。
书生说,人和猫之间没有区别,生来便是孤独,生来就在流浪,谁都一样。当时我正推着他走在玄武湖的堤岸上,远处辉煌的灯光映在湖面也映在我俩的脸上,像是一排探照灯照得我们体无完肤。我说你尽胡说,哪儿流浪了,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就像你,每天还能读书。你见过捧着书埋头苦读的流浪汉?他没回我,眼睛直盯着湖面,隔一会儿,说,给我捡块石子来。他拿到石子就用力抛出去,一道弧线落到水里,溅起些水花,咕嘟两声,没了影。我说你这算什么,他说没什么,我就想看看我的人生会落到哪儿去。
书生走后的第二天我读了那首《九月》,读到那句,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跑到窗户边上,朝着外头放声大喊,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
那晚我做了一梦。我梦见自己开着皮卡载着书生行驶在川藏线上。他把黑框眼镜摘了,换了双墨镜,腿也不瘸,腰背挺直,路的尽头是太阳,路的两边是雪山绵延。书生坐在副驾上大声地唱歌,唱的就是《九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醒来时我的胸呀背呀都被汗淋湿了,浑身酸痛,无力反抗,一个人缩在家里,烧了一整周。那一周里我反复思考着书生曾说过的话:我的人生会落到哪儿去。我想了很多种可能也没有得出结果。或者说这问题就没有结果,天生如此。
病好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书生。买了只百味鸡,两瓶雪花,用塑料杯子装着,一杯在墓前洒了,一杯一饮而尽,喝完点根红南京,蹲在碑前闷头抽。我记得第一次和书生喝酒是在刚把海子接回家的时候。路边随便找了家大排档,点了些串儿,也是一人一瓶雪花。可能是腿伤的缘故,他酒量很差,两三杯脸就红透了,再喝就有些神志不清,我看他晃悠悠拿不稳酒杯连忙叫停他。我说你都醉了,我把你送回去吧。他说你也把我当残疾是吧?我是有点瘸,但我只要还走得动路就不要人背。我说我哪句话说要背你了,他直晃脑袋,说,我不管,你们都把我当废人。说完他狠狠掐自己的腿就像是要把它拧断。
如今我蹲在墓前,他的话像耳光让我脸颊剧痛。我拍着地上的石砖像是在拍书生的肩膀。我说海子我有好好照顾,它可想你了,你走之后它三天不吃不喝蹲在空调后面默默流泪。我说你叫我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完了,你没骗我,确实过瘾,读罢像是脖子挨了一针麻药,坐在那儿半晌动弹不得。我说你错了,你不是废人,我们才是。你的人生已经落地而只有废人才不知道何时着陆。我还有很多想说想做的,但不知怎地酒劲顷刻间就顶上额头。我撑着最后一点力气,起身,拍拍灰,端起酒杯,朝墓碑用力鞠了一躬。
耳畔是天地之间的一声呜咽。
…………
全文首发于《四川文学》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