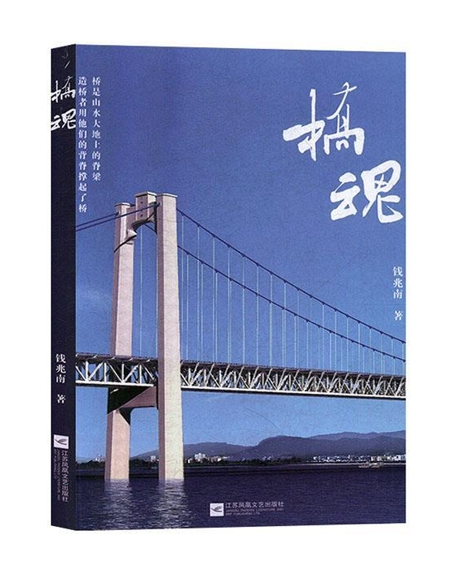
钱兆南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作者简介
钱兆南,原名钱俊梅。江苏海安人,中国作协会员。创作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若干。出版“三农”长篇纪实文学《跪向土地》《天时谱》《桥魂: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我在,我们在》。在《天涯》《作品》《雨花》等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多部作品获奖。
在泥尘中的行走
文 | 钱俊梅
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书,从动工到出版用了十年时间。为什么我要把书名确定为《跪向土地》?是因为每一次回到海安老家总是铁将军把门,母亲必定在田里劳作,蹲在田里时间久了,她的膝盖吃不消,就跪在田里。
母亲在田里摔断了腰椎,从此瘫痪,一直到亡故。
用十年工夫去磨一本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泥土是有记忆的,那么普天之下的泥土与人一样,特别是对母亲的记忆。唯有回到故乡土地,才觉得魂回到肉身。
写这本书的那年,家中第五次建房,我却很少回家帮助母亲,经常一个人在乡村行走。天黑下来,我像天上流放到人间的星斗,在田野深处无力地闪烁着。那时,家中的老房子拆了,借邻居家的厨房烧饭,母亲数次摔得鼻青脸肿……这都是我的罪孽。
天乾地坤,为母亲写一本书,天经地义。忆亡故三年多的母亲,她一个人在田野里与泥土对话的情景,道不尽的是土地与农民同生共死的悲怆之情。在母亲下葬时,我将这些年出版的三本书放进盛放她骨骸的缸里,缸是爷爷买的,这缸盛过水,装过谷子。此举似乎是在为自己离开母亲,把她一个人留在泥土上受难而赎罪。父亲说,母亲生前天天泡在田里,没空读我写的书,到那一世她不要种地了,有的是时间读书。
从开始田野观察调查,行走,拍摄,访问,几年间拍坏了两个相机,两部手机,雨天行走时,腿摔伤过。38度的高温在水稻田中行走,去镇江大路镇万顷良田中的“99间半”清代民居走访,热得中暑。当书呈现在自己的面前,内心感到庄严,肃穆。
事实上,这本书如已故小说家、出版人黄孝阳先生所言:一本书,要像一棵树一样从地里长出来的。当年他和王十月一样,发现了“这棵树”后很是惊喜,并成全了这本书。在此感谢这本书的两位贵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义为“田野观察者”,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草根作家”?
盘古开天起,大地上可能只有草,没有所谓的庄稼。田野与每个人的生存休戚相关。人类的战争,应该是从人草大战开始的。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逐渐演变成人和草灾、虫害的战争。明知道是对泥土的戕害,却一意孤行,大量的除草剂和农药涌向田园,人类的生命不同程度地受到威胁。因此,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劣,需要唤醒田园上的种植者们,需要田野以外的观察者的介入。
一些同道中人曾善意地提醒我:“这么拼命,力用尽了,心会碎的。如果以小说的形式书写,要省多少力气,不值得。”尽管如此,我一分钟也没动摇,就这么一门心思扑了进去,远离人群,越走越远。有人问,书中人物水花是不是你自己?我说,是,也不是,水花是一代农村青年的命运缩影。但这个社会,像水花这样绝决的人已不多,她属于稀有品种。她是一个内求的人,而现实世界中的人习惯了外求。
直到2016年这本书被多家出版社退稿,我面对一堆稿纸嚎啕大哭时,有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呼唤着我:你要走的路还很远,不能停下来,否则对不起他们。于是,我沿着村民们的脚步去了离家很远的工地现场,去见证农民工的喜怒哀乐。
走进工地,是宿命,也是使命。为了写工地现场,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自己与工地现场捆绑在一起。从一名施工现场最底层的资料管理员开始了解工地的肌理,在施工现场忙碌的间隙,用手机抢写了近10万字的工地笔记。工地场犹如战场,用三年时间走进国家建桥工地,这些都是日后创作的素材。工地上有我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们,走近他们如走近自己的心,渴望通过自己绵薄之力为他们做点什么,哪怕给他们带来些许的慰藉,那将是一个卑微的写作者最大的幸福所在。他们说,一直希望有人写写他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在山河大地的荒野中一直在等着一个忠诚的写作者的出现,去倾听他们在江河大地上迁徙着的流浪故事。《桥魂》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采写工地现场时,母亲病重瘫痪。我在母亲的床边照顾三年,将电脑架在母亲的护理床边没日没夜地写。病中的母亲为了不影响我写作,哪怕疼着,渴着,也一声不吭,默默地盯着我长久地看。采写的过程中,因着自己和他们的意志力,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当苦成了生命中的常态时,所有的苦乐都与他们捆绑在一起,与他们共同进退。无数个不眠之夜,母亲的病床边,在圌山脚下江边集装箱的值班室里,翻阅他们每天的施工日志,沿着他们记录的蛛丝马迹,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内心是庄重与自豪的。
评论文章
文 | 纪红建
钱俊梅的《桥魂》是一部记录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建设艰辛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令我惊讶的是,作者并不是传统地以大桥建设时间为线索,而是以内在的精神为逻辑,以生动、细致、深刻甚至散发着人间烟火气息的故事进行呈现,让整个内容饱含人性关怀和思辨色彩。我又阅读了她的散文集《跪向土地》,这是一部文笔优美而老道,充满悲悯情怀、忧患意识、反思意识的优秀作品。钱俊梅说,她是一名田野观察者。其实她不仅仅是一名观察者,更是一名思考者和记录者。她创作《桥魂》,并不是简单地写大桥的建设,而是以一名观察者、体验者、思考者的身份进行深刻而又温情的开掘,这让《桥魂》视野开阔,有着别样的韵味和景致,写出了大桥人“跨越千堑,超越自我”的精神。
钱俊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展现了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的良好品质。早在2016年,她就孤身一人到徐州沛县郊区的一个房建工地,隐藏自己的身份,当了一名资料管理员,悄悄记下工地上的一切,在两个月时间里,她在手机上记录了10万字。为了采写《桥魂》,她独自深入施工现场,拎包入住,来到一线中的一线,与建桥人一起工作与生活,切身感受大桥人的24小时,从每一滴汗水里发现故事,于每一次微笑间体会感动,在每一项成果中感受奉献。慢慢地,大桥人把她当成了自家姊妹,大桥人的父母姊妹们如她的父母姊妹一般,她陪伴他们一起上夜班,攀主塔,爬南锚,走引桥,在江边零下10度的寒风中穿梭。有一个细节令人感动:2019年正月初三,一场大雪席卷工地,钱俊梅来到工地,放下行装,直奔南锚碇的施工现场。当天夜晚零点,零下10多度,她又上4号主塔,风大得吓人,她的眼镜都被吹落江中。为了跟踪采访测量员徐飞、余国元的测量团队,她一直伴随到下半夜。全长2000多米的猫道,边跨45度,她独自从南锚到北锚,再原路返回。在整个叙述中,作者始终在场,始终以参与者、当事人的身份出现。在场不只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责任。
钱俊梅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和敏锐的洞察力。作家要善于从身边的人和事中发掘时代的烙印,风起于青萍之末,报告文学作家就是要做善于观察青萍之末的人。《桥魂》中书写的人物有70多位,作者都较为成功地刻画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生动,情感也极为真挚饱满。这得益于作者深入一线,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对大桥建设中每个项目,甚至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
钱俊梅具有较为深厚的散文功底和高超的叙事能力。高超的叙述能力来源于她真正做到了深入生活,还有她较强的逻辑思维,特别是她作为散文家那诗意而又接地气的语言,增强了作品的叙事能力。如“雪中有桥初长成”一节,作者选择了一个大雪天深入一线细致观察,用散文的手法详细刻画了施超、孟师傅、马海什古木等人物形象,让作品充满诗意与韵味,作品感染力得到极大提升。又如“钢筋厂里的钢铁侠”一节,作者用散文手法和较强的叙事,成功刻画出王云霞、郑心乐鲜活的形象,让作品的文学表现空间更加宽阔。
钱俊梅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出色的思辨能力。钱俊梅是一位反思意识很强的作家,她用叙事和议论等方式对“桥魂”进行了全面阐释:是责任和使命,也是顽强与奉献,还是小家服从大家,更是质量、良心、创新、突破。什么是桥魂?钱俊梅用思辨的思维作了很好的回答:“一座座大桥,其实就是一代代造桥人用血肉化成混凝土,用筋骨化成钢筋的魂,用强大的意志筑起的一座座大桥的丰碑。”
《桥魂》是一部深刻而又温情的优秀作品,表达独特,思想独立,而又饱含人性关怀。《桥魂》写的是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实际上写的是时代的变迁。桥梁,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自古以来就承载着连接两岸、沟通人心的重任。在现代社会,桥梁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城市发展的象征,它们以独特的姿态横跨江河湖海,连接着现实与未来,书写着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
钱俊梅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敢于冒险、不畏生死的勇气。她具有忧患意识,有强烈的反思意识,有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不迁的品质。她善于取长补短,完全有能力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一名视野开阔、表达深刻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